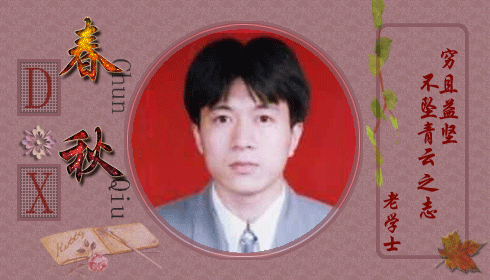【丁香收获】前面就是麦季(散文)
【丁香收获】前面就是麦季(散文)
![]() 不用眼睛瞅,只要嗅到空气里干焦的味道,全村的人没人不晓得:麦稍黄了。
不用眼睛瞅,只要嗅到空气里干焦的味道,全村的人没人不晓得:麦稍黄了。
村里人管接下来的这段时光为“龙口夺食”。谁说庄稼人没文化,说话粗野?他们才是“咬文嚼字”的行家呢。许多时候,文人讲半晌说不清的事,他们一个词,或一个字就道明白了。这里一个“夺”字把整个村庄的紧张、繁忙、焦灼、劳累状态,活生生地呈现到了你的眼前,换哪个字能有这精妙?
其实,“夺”的准备人们早就着手了。
我们沿河槽一带最大的庙会是旧历三月十八的广胜寺庙会。起了会,方远四五个县的人都往霍山根麇集。庙会期间,要祭水神,唱大戏,闹社火,诵经礼佛;各路商贾,各样小吃摊子在道路两旁拖了不下三四里长。但明眼人不难看出,庙会的“核心”还是物资交流。庄稼人的眼睛始终盯着镰刀,扫把,麦绳,木掀,草帽等割麦必需的农具物什:不称手、不周整的家具万万不能要,耽误功夫事小,惹人笑话可损人的“行情”哩。日近黄昏,该粜的五谷杂粮出手了,该购置的相宜家伙也弄到了,最后再割几斤肉,称几斤蔬菜,就满载而归,算是完成了“远程科目”。
回到家还有不少营生等着呢。
婆娘娃娃在屋内忙着腾瓮、修屯、补口袋;男人们则挑水的挑水,驾牲口的驾牲口,忙着磨场。一冬一春堆放了禾秆、柴草沆沆洼洼的场院不清理、平整、碾压可不行。
汗水浇灌着兴奋与喜悦的花朵。
希望款步而来。
急性子小锁了儿,一天两次往地里跑,察看麦子是否黄了,干了,可以开镰了。见多识广的玉柱,嗔道他“烧包”,他就讪笑道:“麦黄一晌咯!”
实际上村里心焦的人有的是。有的人“青黄不接”瓮底朝天了,有的要补上年塌下的窟窿,有的指望粜点余粮供孩子上学、盖房、娶媳妇呢!他们祖祖辈辈就懂得,神仙皇帝全靠不住,土地和土地上打下的那点吃食才是命根子!你与他们处交深了,你就不会嘲他们把简单而苦难性的劳作当作狂欢的做法了,你也就清楚,对他们来讲“泼水节”“愚人节”,还有“斗牛”“赛龙舟”什么的,是不能顶“干粮”的。正由于这个缘故,他们说的、用的、瞅的东西中都带有那么一股“土”味和“粮食”味。
大自然是最讲秩序的。我们村的麦子毫无例外年年都是从西北角的“风死疙瘩”开始的。也不知道是那块地地处高垣,干旱,风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全村第一镰是从那里割起的。村里人既聪明又固执,他们总结出了一套很实用的经验和规律,他们也只相信这一套。比如,不管你气象预报咋说,他们只眺望东边霍山顶上的云雾变化:“拦腰一道,大雨来到”“东山戴帽,天火烧焦”。“风死疙瘩”是麦收的晴雨表。郭顺是那块地的主人,左右邻居,就盯着他行事。
“兵贵神速”。平常松松垮垮的庄稼人在某个清早竟然一个不拉地出现在麦田里。
这真是个大忙季节呀!街坊邻居,包括一家人碰了面打招呼的用词简洁到了极致,有时干脆就一声不吭了。在没有收割机的年月里,全村的麦子都要一镰一镰地割。在毒日头下,只有嚓嚓的镰刀声。挥镰的人是顾不得用毛巾擦汗的,咸涩的汗水流进了眼睛,他们就拿食指刮一下,甩掉,继续弯腰干;口渴了呢?也好办,有“长脖子罐子”等待着你呢:地头不是有渠水流过么,你趴在渠垄脑袋伸下去,管叫你喝个够!小孩子腰酸了咋办?也好办,大人会说:“小孩子哪里有腰?静静地吧。”
忙归忙,但一点不乱。
一家人分工很明确,也很合理。青壮年在前头“拉巷子”,一路领先,为后面的人“打茬口”,辅助劳力跟在后面,紧紧追赶——前头的人不能松歇,一缓气后面的人就要拍你的屁股蛋子;后面的人也得欢欢势势地干,不然被“拉巷子”的人拉下老远,邻居就会笑话你,闲下时就不客气地打趣你。婆娘、老人们则负责铺绳、掌腰、捆个子。红隆隆的太阳坠入西边的“老爷顶”了,一家人就收镰刀,开始扛麦个子装车,往家里运输。天再黑,也得打着蓄电灯拉运完,明天还有明天的活儿呢!说到这儿,你大概会纳闷,你们就不吃饭吗?是的,这个季节谁还记得吃饭的事呢!村里人谁不把黑夜当白天得使,不把一个白天当三个五个地用呢?
大人忙的当儿,娃娃们也不闲。
学校照例放假了。孩子们知道,地里除了需要他们“搭把手”外,乐趣还多着呢。比如,镰刀割着割着,一只土灰色的鸟儿就突然扑楞楞打麦丛蹿向天空,你低头一瞧,麦子根儿上准有一窝鸟蛋或几只红压压的雏鸟在吱吱啁啾;要碰见蛇那就更刺激了,村里孩子胆子大的很,见蛇溜出麦根儿,他们就追,追到跟前将蛇的尾巴一提,那蛇扭来扭去,脑袋一仰一仰的,终归徒劳。这时,已有人挖好了土坑。提蛇的孩子抖抖地将蛇的脑袋放到坑中,其他孩子一齐行动,就将蛇的脑袋埋住了。好戏开始了:露在外面的蛇身拼命地甩动,地上发出啪啪啪的声响……大人与孩子联合行动的事儿是野兔的猛然钻出。只要一听见有人呼喊“兔子”,一河滩的人立刻仄起耳朵,寻声围拢过扑去--其实,村里人对兔子并不稀罕,这么做带有很大的娱乐成分,嘻嘻哈哈地一闹腾,疲乏劲儿,枯燥劲儿就不见了……这些活动一般持续得时间很短,这大概是大人对在学校“圈弯尾巴”孩子的一点犒赏吧,接下来,就得干“正事儿”了。搂铺儿、铺绳、掌腰要干的活儿有的是,孩子们一般都挑选拾麦子。因为这档事儿从祖辈传下的就是计件计酬的。孩子们一边弯腰拣着麦穗,一边盘算着一把麦子多少钱,多少钱可以买一个新书包,买一套小人书……
不仅如此,动物们也很识眼色。你见过那头驴那头马那头牛,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发情跑圈下崽子的吗?绝对没有!它们不是在地里就是在路上、场院里忙着呢。还有那些狗呀鸡呀猪呀它们一下变得懂事了,不吵不闹,各司其职,该干啥的干啥。
割完最后一镰,人们张起腰往往会如释重负地幽默一下:“要知道在这儿完,还不如当初从这达开始哩!”
接下来“中心”就转移到了场上。场上的活儿虽然要比在地里轻快些,不用头顶烈日,赶早摸黑,腰酸腿痛,口干舌燥地“抢死抢活”,但事事繁琐,每件都得赶趟儿,还马虎不得。
麦场里的头一道工序是抖麦。一大早,妇女们顾不得生火做饭,男人们顾不得下地,他们早早就来到了场上。妇女们抓起一把麦子在近靠麦穗的地方用力一折,边抖边放置到一旁,男人们则用木杈杈起抖在地上的麦子抖擞着拢立在场上。一把完了再抖一把,直到将一大堆麦子抖完拢完。抖拢的目的是为了便于通风透气晒太阳。稍迟一步,麦子就发热发霉,再耽搁就费了,焐过的麦粒连猪都不吃。抖完,妇女们就回家去做饭,男人们则下地牉麦茬,等一家子人吃了饭,洗罢锅碗,太阳就升到半天了,这时,男人女人就一起去场上用木杈将麦子再抖擞一遍,让麦子吹晒得再充分一些,越干越好碾。
正午时分,趁着日头正毒开始碾麦。妇女们用木杈将虚拢的麦子拍下去,牲口就进场了。在没有打麦机、割麦机之前,碾场是靠畜力或人力来承担的。通常是将两头牲畜并联在一起,后面拉上碌碡,人牵着牲口的缰绳,从场的一头,向另一头逐渐扩大着半径划圆。碾过一遍之后,人们要用杈将压实压扁的麦秆翻个个儿,这称为翻场。接着再继续碾压。等到麦杆和麦穗碎了,碾场才算完结。接下的工作是起场--起场也有讲究,不能随便把麦秸杈起就走,杈麦秸的时要先抖上几抖,以便将麦秸与麦粒分开。
麦秸杈走,黄澄澄的麦粒就透出来了,那股带泥土的清香也就扑鼻而来。
看看人们脸上那为“色和香”陶醉的表情吧,那才叫喜笑颜开呢!
不过这还不能算“大功告成”。
接下来是起场和扇场。场上需要再次分工。老弱人员开始捞扫帚地捞扫帚,推甬板地推甬板,将麦粒迅速堆成一堆;青壮劳力则忙着抬扇车扇场。这个活儿,至少需要四个人配合,一个人坐在一人多高的坐凳上踩扇车,一个人来回拖簸萁,一个人用木掀铲着麦粒往簸萁里到,一个人在扇车口前用扫帚将细碎的麦秸、麦皮、杂物扫到一边。这个环节有个禁忌:不准人说麦子多啦少啦好啦差啦之类的话。老人解释说:得罪下毛嘴神,他就把麦盗走了。扇场需要的壮劳力多,是个技术活儿,一般的人家独立难以完成,往往几家人搭班子,一家一家地挨着来。受这些条件的制约,往往要白天黑夜地连轴转,人轮流歇着,扇车始终扑沓扑沓地不停。
从第二日起就要将扇过的麦子赶紧摊在场上暴晒四五天。迟上半天麦粒就会发热变味。
摊开麦子按理说有空喘口气了,但庄稼人又嗅到一股温热而酸涩的气味,他们反应过来:棉花该掐顶、除叉儿了。接着又嗅到了一股湿润而青骚的味道:红薯该翻蔓子,水稻该拔草,玉米该施肥了……还有人同时分辨出了甜瓜、花生、蒜苗、山药蛋、药材等等经济作物的各种各样的的味道。
当那种甜腻腻的气味从汾河滩一缕一缕飘来时,庄稼人的耳朵又仄起来了:秋庄稼成熟了!
这种本领一辈接一辈地在庄稼人的骨子里藏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