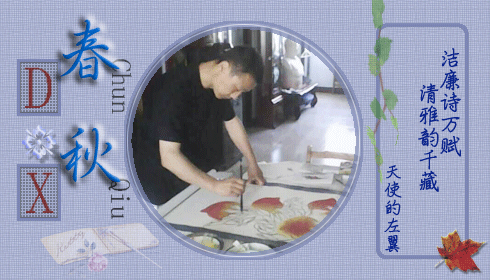【丁香青春】难忘那片梧桐树(散文) ——-----南垣村之四
【丁香青春】难忘那片梧桐树(散文) ——-----南垣村之四
![]() “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从一个普通的农村丫头,到中学高级教师的蜕变,首先要感恩的是我的母校——洪洞曲亭中学。感恩诸位质朴真诚、才华横溢、无私奉献的恩师们。感恩那片郁郁葱葱的梧桐树,以及树下演绎出的许许多多的动人故事。
“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从一个普通的农村丫头,到中学高级教师的蜕变,首先要感恩的是我的母校——洪洞曲亭中学。感恩诸位质朴真诚、才华横溢、无私奉献的恩师们。感恩那片郁郁葱葱的梧桐树,以及树下演绎出的许许多多的动人故事。
初中阶段,有幸遇到班主任冯培先老师,代语文课的董元龙老师,代化学课的周喜乐老师等等,还有想不起名字的恩师。他们或幽默,或严谨,或睿智,或生动。在一双双渴求知识的农家孩子眼里,是神圣、智慧、更是伟岸的化身。“文革”剥夺了我们的学习机会,偌大校园,放不下一张课桌。尽职尽责的老师们啊,不怕打击,不畏批斗,断断续续的课堂教学在那片梧桐树下进行。开完批斗会,还来为我们铺导功课。尽管大字报封门,戴着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有一次,造反派来抓捕正在上课的老师,同学们为了敬爱的老师躲过一场人身凌辱,情急之中,把老师藏在一棵粗壮的梧桐树上,浓郁的梧桐树叶,竟掩护了我们战战兢兢的老师。造反队举着写有老师名字,且名字上有大大的红色“XXX”的大门板来了,找遍整个校园,楞是没有找到“反动学术权威”,因此,我永远感恩那片圣洁正义的梧桐树。
白发苍苍的冯培先老师,二元一次方程式,数轴,“丌的由来”等等枯燥的数学公式,在他的教鞭下竞成了有趣的游戏。仪表堂堂的董元龙老师,深邃的目光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优美词句,典故,故事儿。为了教会同学们学会思考,他在最后一堂课讲了一个“宿娃儿”(麻雀)的故事。老师娓娓道来“人要学会思考。比如,为什么祖祖辈辈称麻雀为‘宿娃儿’?我小时候常常看着屋檐下飞进飞出的麻雀发呆,为找不到答案苦恼。妈妈总说我得魔怔了,人家叫了几辈子,没人把这当个事儿,就你一天到晚刨根问底。”
老师接着说,有一天傍晚,我又坐在门槛上发呆,一只老麻雀站在屋檐下的椽头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那里有一个简单的巢,摇搖欲坠,一会儿小麻雀相继飞向这个家,老麻雀安静了,哦,原来老麻雀是呼叫儿女们回家呢,好温馨的场景啊。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麻雀叫“宿娃儿”了,它们白天在外觅食,玩耍,晚上不是要宿在瓦下吗?“宿娃儿”即“宿瓦儿”的谐音。我高兴得蹦起来:“妈妈,我知道了,知道了。”妈妈正在立炉(厨房)里做一大家子人的晚饭,那能顾上这等闲事儿,她不耐烦地说“又犯魔症了”。虽然妈妈不理解我,但我知道了为什么麻雀叫“宿娃儿”了。这就是思考,同学们,凡事要学会用脑思考啊,董老师的最后一课让我们记忆犹新,懂得了动脑思考的重要。
那个年代,批白专,斗权威,教室里无法正常学习。像课后自习,背俄语单词,游戏活动,忆苦思甜会,大多都在梧桐树下完成。学生食堂与梧桐树连接在一体,饭前排队,敲碗声和着少男少女的欢笑声如交响乐,令人时时忆起,永远难忘那片欢快的梧桐树!
高中阶段,恩师刘文敏,刘宝基,李淑英,张管成,周喜乐,顾佩文等等老师更使我们钦佩不已。刘文敏老师以严厉著称,李淑英老师名如其人。那简陋得无法形容的“延安窑洞”,我们师生同住。苍老的窑洞,见证着一届一届师生的深厚情谊。“熄灯了,不许说话了。”刘老师大嗓门一喊,窑洞静的能听见彼此心跳。
“同学们,快点休息,不要说话了。明天上课怕打磕睡的。”软绵绵好听的普通话,顿时联想到李老师那樱桃小嘴。不管严父般的,还是慈母式的,都是尽职敬业的好老师。安顿同学们熄灯后,老师们也不会休息,常常是挑灯批改备课至深夜。
记得刘宝基老师,不但教会我们一口流利的俄语,还教会我们打蓝球,我们称他是全把式。由于我们不懂事,常惹老师生气,但刘老师爱生如子,从来不跟我们计较。还有晋国宝老师,用带赵城味的洪普话(洪洞普通活),把枯燥的政治课讲成故事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下课前十几分钟,黑板上故事标题穿成串,正是这节课的重点题,(我后来再没听到过那样生动形象的政治课)。
张管成老师幽默生动,物理课上讲匀加速,操一口临汾南县话,如果你们到甘亭挑煤,用上匀加速,刺儿……一下就到了。哈哈哈,教室一片会心的微笑。那会儿冬天取暖,我们挑着筐子到甘亭火车站挑煤回来打煤糕,还有,李铁梅提篮小卖拾煤渣的感觉。挑不动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学着张管成老师的口音“刺儿,一下子就到了”,顿时驱赶了疲劳,一路笑着闹着往学校赶,当然,也有人到了学校,还剩半筐,免不了第二天被罚,继续提篮小卖拾煤渣。
周喜乐老师的化学课更是形象,生动,有趣,易懂,他手中的教鞭如磁铁,如魔棒,伴随着他磁性的语调,我们的眼神一会儿到黑板,一会儿到玻璃,目不暇接,如看魔术,玩游戏。中掌握知识,记得很牢固。还有好多好多优秀老师,有趣的事。
我教坛生涯四十年,不管如何教改,总在固执的模仿我的老师,老师的优秀品质,渊博知识影响伴随了我的一生。感谢您,我敬爱的恩师。忘不了,在那片古老的黄土地上,在那座座简陋的平房教室里,在那郁郁葱葱的梧桐树下,活跃着一群不图荣华,不计名利,不计报酬的才华横溢的优秀老师们,曲亭中学乃卧龙藏虎之地。因为有了你们,曲亭中学当年领先洪赵,声震平阳,誉满三晋,各地学子不远万里慕名求学者比比皆是。
我终生钦佩的老师,您尽毕生的心血,滋润每个学生的心田,您倾其所有,苦口婆心的传授知识。你们像那一棵棵梧桐树,默默坚守着这片黄土地,夏天为我们撑起一把大伞,冬天为我们遮挡一地雪雨。我永远永远想念那片梧桐树,难忘让我梦牵魂绕的母校,为我们呕心沥血的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