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风】车轮滚滚(散文)
【西风】车轮滚滚(散文)
![]()
现在的中学生,恐怕没几个知道独轮车。我们的子侄辈,大多对独轮车很陌生。然而我们这一代,尤其是出生在农家、做过农活的,回忆起当年的务农生涯,无不对独轮车情有独钟。因为,木制的独轮车,曾是一种既经济而用途最广的运输工具。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我老家崇明岛上,大部分农家都有一辆独轮车。
我对独轮车的最初印象,定格在我六、七岁时,全家去猛将庙走亲戚。亲戚家房屋坐向、大小、家境如何,事后早就毫无印象了。唯有坐在父亲推的独轮车上的感觉,却永远铭刻在脑海深处;临河的土路上,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微微弓着,双手紧握独轮车把,不紧不慢地往前推。母亲抱着出生不久的妹妹坐在车的左侧,我坐在右侧。大哥、二哥和三哥紧跟在独轮车的后面,步行。
其实三哥只大了我两岁,却没捞到坐车的机会,只能嫉妒地跟在车后,捣腾着小脚一路紧撵。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暗恨过我。事后回想,父亲让我坐车,并不是因为特别疼我而让我享受特殊待遇,而只是为了平衡手控的独轮车,推起来省力些。
时近初冬,独轮车在高高的河岸土路上一路往北。远处,成片的冬小麦和油菜一片嫩绿。再远处,则散落着一个个被杂树、竹园庇护着的宅子。独轮车随着父亲的步伐一起一伏地颠簸着,我好似坐在摇篮里,享受着温暖和煦的阳光,很快就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然而,父亲的一声咳嗽惊醒了我,我突然觉得身下的独轮车在一步步地后退,竟不知要退到什么地方。我惊骇地睁开眼,噢,车子不仅没有后退,还在继续往前滚动着。于是我再次闭上眼睛,真切地觉得车子又在后退了。这试验我悄悄做了好几次,所得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于是我好奇地扬起脸问父亲:“阿爸,为啥我闭上眼睛就觉得车子在后退呢?”
父亲还没来得及解答我的问题,大我两岁的三哥终于按捺不住,冲到我旁边咆哮起来:“坐就坐了,还说啥屁话!你不想坐了就下来,让我坐一会。”
记忆到这里戛然而止。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独轮车的印象越来越多了。然而,最深刻的是,每当阳春三月,桃红柳绿时,南归的燕子在金色的油菜花海上恣意滑翔,善啼的八哥躲在绿荫深处婉啭酬唱。男女社员换上春装,散布在大田里,热火朝天地春耕。闲置了一冬的独轮车一齐上阵,将各家各户沤了一冬天的厩土从猪圈、羊棚里起出来,一一装到车上。然后,推车人迈着轻快的脚步,手中的独轮车被推出一路欢歌,穿梭在被嫩绿色漫延的田埂上,将一筐筐厩肥运到大田里。
金秋十月,天高云淡,大雁南飞,大片棉田盛开着洁白蓬松的棉花,好似铺了一张雪白的巨毯。已经收割放倒,并经过多日暴晒的稻谷铺满了块块大田,空气中弥漫着成熟稻谷特有的香味。这时,农家所有的独轮车一起出动,从大田里抢载稻子。于是,一长串独轮车,在小山似的重负下,车轴和车碗间极力摩擦着,发出各种“吱吱呀呀叽叽嘎嘎”的声音,汇成一曲独轮车大合唱。长长的车队走在坚硬的田埂上,车轮滚滚,扬起一路风尘,向远方的打谷场行进。
解放前,由于崇明岛四面环水,与外界的交通极为不便,岛上鲜有汽车,全岛商家绝大部分的物资运送,只能依靠独轮车。因此岛上有很多农民靠推独轮车为生。
我父亲不止一次跟我们叙说:1910年腊月初的一个傍晚,我父亲出生时,我爷爷却推着独轮车在三十里外的海桥镇送货,直到半夜里才顶风冒雪赶回家里。
我叔叔几次跟我说过:他自十五岁起就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追随着村里的有财、有福、宝根、宝祥等一帮本家哥哥,推着满载货物的独轮车,常年往来于庙镇-桥镇-堡镇等地。桥镇离庙镇约三十里,当天一个来回比较轻松。但堡镇远在八十里外,推车人四更天就得推着货物动身,紧赶慢赶,中午时到堡镇,卸下货物立即再装上其它货物,继续赶路,约二更天了才能回到家里。
叔叔说,解放前的公路状况很糟糕,大多是泥路。风和日丽时,路面上总有深深浅浅的车辙,稍不留心,重载的车轮就会别到车辙里,一把没挽住,车就翻了。春雨绵绵时,路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坑,泥泞不堪,胶粘缠裹。空身走路尚且视之为畏途,推车人冒雨蹚水前行就更是辛苦了。而且沿路有数不清的木桥、竹桥、石桥,由于年久失修,走上去让人提心吊胆。
那时载各种货物的独轮车在狭窄的泥路或桥头相遇,根据车上装载货物的价值、补救难易,形成推车人之间必须严格遵守的避让规则。比如运柴车必须让运棉车,因为棉包掉进河里立即受潮,纺织厂就不收了;运棉车必须让运油车,万一摔坏了油篓子,油洒到泥路上没法舀起;运油车要让运瓷车,因为瓷器价值比油高,还易碎。如果谁违反了这约定俗成的规矩,导致对方的货物受损,违反方就得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
我们杨家,因为出了几个人高马大,膀圆腰粗,喜欢打抱不平的大力士,颇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人称“杨家将。”
有一年深秋,“杨家将”的车队行进到离施翘河不远的浪搭桥,却见桥畔停了几辆车,一辆装着稻谷的车翻在桥头,桥上围了一帮推车汉子,正指着桥下起哄。
“杨家将”们眼见不能过桥,就地停好车,有财吩咐我叔叔看车,自己则领着其他弟兄走上桥头,拨开人群,往桥下看,只见一个身材矮小的推车汉子,在河中哭丧着脸,挣扎着想游到河边。
有财问看热闹的人:“这是咋回事?”
有个推车汉子乐滋滋地回答:“那个乌虫(崇明土语,骂人话;傻子)推车不长眼睛,站在桥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上去跟他理论,他也听不懂。于是我们就教训了他一下,让他以后长点记性。”
有财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问:“这么说,是他先到桥头?”
“这……就算他先到,他推的是稻谷,按规矩就该让我们的运棉车。”
“你们看他孤身一人推车,就拿这歪理来刁难他。兄弟,这事做得可不厚道。”
“那……稻车让棉车是规矩。”
“不按规矩,就得被推下河?”
那个推车汉子明显感觉到有财的话里藏有杀气,不觉胆怯了,就咕哝了一句:“又不是我推下去的,你盘根问底的想干啥?”
这时,有个满脸横肉、膀大腰粗,二十出头的愣头青,头戴一顶软塌塌的破草帽,敞着陈旧的老布褂子,露出胸前一大片又密又长的胸毛。他把双臂往自己胸前一抱,横在有财面前,睁着牛卵般大眼,用破锣嗓子吼道:“是谁他娘的裤裆烂了,钻出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乌虫来管闲事?那小子不长眼,你也不长眼?”
有财斜视了对手一眼,道:“小兄弟,大概你出道不久吧,出口就伤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大家都是穷人,吃这碗饭都不容易。虽说推车人有避让规定,但也有先来晚到的说法。他先上的桥头,你们就该奉行上桥车须让下桥车的规矩。你们仗着人多势众,难道让他倒推着车退回到桥下?你是长眼的,可你见过倒推车么?”
愣头青一拍自己的胸脯,喝道:“看来你没见过,今天就让你开开眼!”话音甫落,他伸出右手,抓住有财的衣领,使劲一推,道:“你下去跟他搭伴吧。”却不料有财早就防着这一手,说时迟那时快,疾出右手扣住对方的右手,使劲一拧,化解了对手的力道,顺着对方推送的力量,将对手轻轻一带,同时一闪身,让过收脚不住的对手,左手顺势在那前扑的愣头青后背上一拍,喝道:“还是你下去吧!”只听“轰隆”一声,河水溅起老高。一眨眼功夫,那个愣头青被有财摔到河里了。
几个同伴眼见愣头青被打落河中,赶紧奔下河滩,扔出手里的推车麻布绳,七嘴八舌地喊他快接住麻布绳,想拉他上岸。有财站在桥上一声暴喝:“谁也不许拉他上来!谁不听,我就让他也下河尝尝不长眼的滋味!”
河滩上的几个施救者,果然收回麻布绳,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过了会,其中一个年约四十左右的推车汉子仰着脸,拱着双手对桥上的有财连连作揖:“大哥,咱们今天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干起自家人来了。大家都是吃这口饭的,风里来雨里去,其中的辛酸劳累,旁人不知道,难道我们也不晓得?谁家里没有几张嘴等着吃喝呢?万一谁有个三长两短,一家老小就得活活饿死。大哥,那年轻人是我侄子,确实出道没几天,不懂道上规矩,也不听我的劝,一时冲动,动蛮将人推下河,原是他的错。我代他向你、向那位弟兄赔礼了。大哥你是个冲州撞府的真汉子,不与孩子一般计较,你就高抬贵手放过他这回吧。那位弟兄湿了衣衫,我们凑钱赔付。”
有财哼了一声:“这位兄弟是明白人,晓得我们推车人的不易。别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可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咱们今后还得在这条道上寻饭吃,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凡事不要做绝了。”
愣头青被拉上来后,面红耳赤地朝有财作了一揖:“大哥,是我不对。今后再也不敢耍横了。”
那个身材矮小的推车汉,接过众人凑给他的损失费,抱拳对着有财一躬到底:“唉,谢谢,谢谢大哥!我今天遇到好人了,遇到好人了。”
在旧时的崇明岛上,独轮车绝对属于家庭重要财产之一。当年邻村有弟兄俩,父亲死后闹分家,都想独占父亲留下的独轮车。于是,两家人反目为仇,路上互相碰见,如同陌路人般各自扭头,不置一语。村干部上门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弟兄俩谁也不让步。于是,他俩的老娘舅亲自出面协调了,拿起锯子将车架和车轮一锯为二,喝令两外甥各拿一半。在围观的村民们的哄笑声中,这辆车子的归属权才得到彻底解决。
改革开放后,随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开发,各种现代化运输机械纷至沓来。于是,曾经在中国大地上纵横了两千年左右的独轮车,终于被效率更高的汽车、轮船、火车挤出了历史舞台,躲进黢黑的柴草房里,或者被丢弃在日渐颓败的竹园里,任由风吹雨打,日晒霜浸,让时光无情地刻蚀,浑身长出惨白的霉菌,静悄悄地腐烂,终于化作一堆粉末,融进土壤里,彻底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有时我骑行在猛将庙附近宽阔平坦的公路上,在高大的行道树交织而成的巨型绿色拱廊下,恍惚又看到了父亲沿公路右边,推着独轮车前行,车上的母亲抱着妹妹,三个哥哥紧跟在父亲身后亦步亦趋。我脚下使劲,想追上那辆独轮车。因为我觉得车上那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是那么的陌生,与我根本不像。
可惜,幻觉总不能当真。六十年一晃而过,父母都已作古,独轮车也在崇明岛上绝了踪迹。当年丰收后车轮滚滚的热闹场面,旧社会里推车人的艰苦生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在人们的记忆里淡化,终将烟消云散。如果想一睹它的风貌,大概只能到各地的风俗展览馆去寻觅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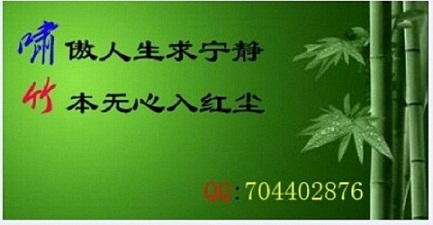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