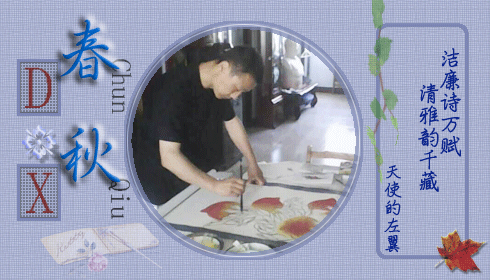【江山多娇】冬天里的一碗温暖(散文)
【江山多娇】冬天里的一碗温暖(散文)
![]()
这几天是十几年来气温最冷最冷的,老人们被孩子管束着不得随便外出。
冬天里,人们都盼望着冷起来,冷了好,冷了好!麦盖三层被,枕着馒头睡。因为农民有个说法,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暖季积温不高粮食收成不好,这是连贯性的问题,可是,天冷了,有些人吃不消。大雪封门,足不出户,平时常来常往的老哥们儿老姐妹儿,几天不着面儿就想得慌,日子长了总惦记着是回子事儿(心事儿),就像儿时的发小,顶价一块堆(在一起)玩耍,一会儿看不见就心里不踏实,非得疯一阵子闹腾累了过瘾了才罢休。
父亲在家里说一不二,谁也拗不过他的心思,无论冬夏寒暑,只要是没有要紧事,撂下碗筷,就到户外活动去了。没人能约束他,说急了他眼珠子一瞪,若是哥哥姐姐巴掌就落下去了。好在每一场大雪过后,庭院里大街上,家家户户都清扫得干干净净利利亮亮的,要不是风大天冷严防感冒,出去走走,对老人有百利而无一害。父亲出门遛弯儿,母亲离不开身,在家屋里院里的紧忙乎。她那几个老姊妹,都知道母亲成年到辈子忙活,没时间串门子,就都来我家跟母亲唠嗑聊叙家常俚短。
人说“吃惯的嘴,跑惯的腿”,聊天唠嗑也是一样的习性,经常在一起的伙伴儿总是忘不下。这时候,母亲又在自言自语了。“也不知你王婶儿忙啥哩?这都好几天了,连个人影也没露。待会儿,得去看看,别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不自在了。唉,这人要是老了就不禁镇乎,最怕有个三长两短,自己遭罪不说,还叫孩子们担心害怕受张罗。”我在里屋听了母亲自言自语,不知道该插句什么使她开心的话,也不由得为王婶儿捏一把汗。因为这几天太反常了,年轻人都还怕冷呢,何况七老八十的老年人。
王婶儿跟母亲一样,含辛茹苦一辈子,到这时也没有闲时候。王婶儿老伴儿死得早,跟儿子住对面屋分灶另过,自己养着几头老牛,五冬六夏地忙碌,一年到头繁育几个牛犊,挣几个零花钱自给自足。几年过来,没磕着没碰着,没病没灾的,日子过得也算安逸自得其所。
唉,如今的孩子婚后过起自己的小幸福,闪开老人家在一边独居,大家都如此,没理由褒贬时尚的事情。人活一辈子,就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坚强到老。无论风里雨里,自己身体好就是硬道理。
我怕母亲不顾天寒地冻去看望王婶儿,嘱咐母亲在家听信儿,我先跑一趟去看看王婶儿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有需要,再让母亲亲自前往探视。母亲满口答应,我抢先一步出了家门。走在大街上,有房屋挡着风向,没觉出多么冷,毕竟是东北人有一身冻死迎风站的傲骨。拐过街口,刺骨的北风顺着街筒子撞到身上,只需你轻抬脚步,就有一只巨手推脱着你,不用花费一点力气,就可以轻松向前挪动身体。我的家向来是母亲搭理,暑天凉爽清洁,冬日温暖舒适,北风还没刺透棉衣,我还没觉出冷来,就已迈进王婶儿的家门。王婶家的院门敞开着,看家狗用铁链子拴在角落里,与主人交好,畜生也摆出友善的姿态,摇头摆尾地“哼唧”着问候。我没心情搭理它,三步并作两步,开门进屋,直奔东侧房间。
屋里静悄悄的,似乎主人不在家,我还是推开里间屋门。一股闹不腾的味道直钻鼻孔,并没有扑脸的暖热,屋里不暖和也不算有多冷,回首望望灶台里一膛死灰,锅灶一副清冷肃静,说不出主人多久没有光顾了。我转回头望向有些昏暗的火炕里,借助透过几层御寒蒙窗薄膜的光线,看到一位老人瑟缩在那里,陈旧的棉被覆盖在身上,一头花白的乱发扑散在枕头上,一张黑瘦的被岁月雕琢的面庞,隐含在发迹被褥和枕头之间,显得尤其瘦小。只见她呼吸均匀,睡在梦乡里,竟未察觉有人来到近前。我没有吵醒她,轻轻伸手探视褥子下面的温度,不凉也不热,我不由得一嘬牙花子。
“老人火力弱,这温度怎么可以?”
我和王婶的儿子一起长大,平时不分你我,两人在一起属于有饭就吃、有活就干那种,所以我也不喜外(不把自己当外人),在院里踅摸了一抱柴火,填到灶坑里,找到打火机点燃。掀锅准备添水,却发现锅里有半碗疙瘩汤,添了水把碗架在锅梁上。正忙着,听到里屋一阵“咳咳咳”的咳嗽声。冲到屋里一看,“哎呀,妈呀!”咋还可屋子烟岗岗的了?王婶儿已经下了炕。
“大婶,我寻思给你烧烧炕,这事儿闹的!一屋子烟了。”
“咳咳,没事儿,咳咳咳……怪我没收拾好烟筒……咳咳,不好烧。”
“哎呀,这屋里没法待了,先到我家坐会去吧?我把屋子烧暖和了再回来。”
我们正说着话,母亲赶来了,死说活说才把王婶请到家里,中午吃了葱花热汤面才送她回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屋子给她烧暖了。
“大婶,她这是咋的啦?”容等闲暇时候,我问母亲。
“嗐!岁数大了,食嗓细(脾胃不快活),几顿吃不下饭就饿垮了。”
“怪不得她在炕上躺着不动弹。”
“两天没吃东西,老牛跟着饿了一天。这不今晚上,老五给他妈做了一碗疙瘩汤,你王婶一高兴,就着泪珠子一口气吃了半碗,刚才还端着面条夸儿子孝顺哩。”
“一碗疙瘩汤还……”
我鼻子一阵发酸,父母都是好糊弄,儿子只是一丁点好处就非常满足了。这算什么孝顺?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要儿女有什么用,还不如当年与老公做了丁克享清福哩。我忽然想到了什么,又问母亲。
“老牛呢?我咋没看见她家牛呢?”
“唉,老五跟老婆商量妥了,牛由老五经管就算入股,每年分红,你王婶放不动牛了,一律听喝(顺从别人的意见),只求养老就行。”
“这,哈哈哈哈哈!”我实在憋不住大笑,这应该是最好的结局了吧。
人都说父母能养十个儿女,十个儿女养不了二老爹娘,可见一斑。不过,眼下这事已经相当不错了,毕竟一碗疙瘩汤还沸腾着孝心的热度,那一份母子情依然健在,那一点做人的根本依然尚存。相信黑发人敬给白发人的,不只是令老人动容,也应该是感动自己的一个举动。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无论严冬多么寒冷,一碗疙瘩汤的温暖,就能暖热一腔冷血,就能复苏一颗向善的心,就能温暖一个漫长的冬天。
一碗疙瘩端上来,父亲老泪流腮帮。感激儿子孝敬好,吃在嘴里甜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