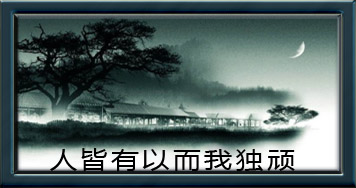【流年】饺子(随笔)
【流年】饺子(随笔)
![]()
民以食为天,天是崇高的,中国人敬天,于是中国人从古到今在吃食上下了不少功夫,同样的粮食和菜蔌,总能变换出数不清的花样,形成了一门研究不尽的饮食文化。
说说饺子。
童年,来路那一头,遥远的记忆,但清晰如昨:饭后出门玩耍的小伙伴喜欢抓堆儿,常常听到有人显摆:“俺家今天又过年了!”那就是说他家吃了顿饺子。其实不过是地瓜面包的蔬菜馅,肉是谈不到的,可能有鸡蛋,或许有少许油。这就是说,无论什么面和什么馅包成的饺子,都可以当成最好的饭食看待,因为饺子名称好听,吃起来便也别有一番足以夸耀的味道。那时,大多数人家唯有过年才可以吃到饺子。
饺子历史悠久,据说它最初的名字是“娇耳”,乃“医圣”张仲景发明的。严寒冬天,他看到许多贫苦百姓缺衣少食,冻得耳朵溃烂,便舍医施药,其中就有“祛寒娇耳汤”。那是把羊肉、辣椒和驱寒药材一锅同煮,熟后捞出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再煮熟,然后连汤一起服食,便会两耳发热,寒气顿消,冻耳痊愈。
不过,也有人说,饺子的历史比这还要久远。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学家曾在新疆一个地方的唐朝墓葬里发现过一种叫做“牢丸”的随葬食物,形如偃月。何谓“牢丸”?明末张自烈在《正字通》里说:“水饺耳,即段成式食品,汤中牢丸,或谓粉角,北方人读角为娇,因呼饺饵,伪为饺儿。”这就很明白了,这“牢丸”就是饺子。既然已经传到了边远地带,那必定已经在内地民间普及了。
饺子把肉、菜、面合而为一,口味独特,便深受百姓喜爱,成为节日的美食。最初是冬至这天吃的,因为张仲景舍医施食是从冬至开始,而冬至又是一个大节气。
中国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秋收冬藏和春耕春播之间需要个缓冲时间,于是年末岁首交替的春节,就逐渐成了每年最郑重的节日,上古时候的祭天祭祖等活动也从立冬向春节转移,称为“过大年”;人们最喜爱的水饺也就从冬至搬到了春节,约定俗成,饺子就成了春节不可更改的主角美食。
中国文人历来喜欢琢磨,尤其在抠词凿句方面,再加上中国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便有人把“饺子”和“交子”联系起来了。大年三十的子时,不是新旧交替的第一个子时吗?“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吃饺子便是“交子”时刻全家人一起最热乎的一顿饭。
“交子”——饺子。
过大年,没有这顿饺子,人们心理上会过不来过不去,贫穷如喜儿她爹杨白劳,即使大年三十也要出去用豆腐换来二斤面,希望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本文作者的家乡胶东地区对饺子尤其情有独钟,除夕晚上、初一早晨、初二晚上这三顿饺子是必不可少的,初五还有一顿。除夕是送旧,初一是元旦迎新,初二是送年(也有初三日送年的),初五那叫“破五”,撤销过年几天的所有禁忌,吃顿饺子以示庆贺。
饺子可谓屡吃不厌,当然馅料是可以变换的。
根据馅料的不同,饺子花色品种繁多,但大致来说总归两种,一种是荤馅,一种是素馅:大凡可以做菜肴的东东都可以做成饺子馅。荤馅可以是肉、肉菜混合,也可以是鱼,或者鱼肉菜混合;那得看荤素馅料味道的搭配是否对味。譬如,牛肉和芹菜对味,羊肉和萝卜对味,鱼肉和韭菜对味,猪肉和一切菜都对味。
素馅,尽管没有肉啊鱼,人们也能对和得异常鲜美;除了青菜以外,蘑菇、木耳、粉丝都属于素的。据说,寺庙里的和尚会把素馅做出鱼、肉一般的口感。
除了荤素两馅以外,还可以偶尔为之包甜饺。那一般是包饺子面皮多了几个,不值得重新拌馅,就可以把炒了当零嘴的花生仁碾压成粉,掺和适量的红糖,捏出特定的记号,和其他饺子一起下锅,盛出来以后,喜欢甜食的大人小孩往往抢着吃,又香又甜别有一番风味。
《聊斋志异》《司文郎》篇提到过“蔗糖水饺”,那个后来成了“司文郎”的宋生“啖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可见甜馅水饺古已有之,不过后来人们习惯了荤馅和素(菜)馅。
吃饺子是有讲究的,譬如过年,如果饺子包得皮儿很薄,下锅以后心里便总有些惴惴地,怕它碎成一锅粥,那就不是圆圆满满了;不过也有办法自我安慰:“挣得不少啊——明年发财吧!”饺子碎了是不能说“碎”的,要用“挣”去替代。再譬如,胶东一带有个话儿,说,“送客饺子迎客面”。那是来远客以后,第一顿饭应当给客人做打卤面条,表示留客——缠住客人的腿;客人第二天吃了饭告辞,那就应当包饺子,吃了以后去他处的路上顺顺溜溜。假如客人只吃一顿饭,饺子就可以以一兼二,既迎客又送客;主人尽了待客之道,客人也留下好印象,心底热乎。
为了渲染热闹欢乐和吃饺子的趣味,除夕或者初一的饺子往往要包进一些其他物事,譬如硬币,谁吃到了预示来年有钱花;譬如糖块、花生、栗子、大枣之类。糖块那是甜甜蜜蜜;花生又名长生果,预示健康,尤其是老人吃到了,便换来一派好心情;栗子,谐音“立子”,大枣和栗子如果都吃到了,那无疑是“早立子”,对年轻夫妇来说,再吉利不过了!
饺子除了经常被称为水饺以外,他还有有很多别名,除了上边说的牢丸、娇耳、交耳、粉角、角子等等古来留下的,还有饺子的近亲如扁食、馉饳也和饺子混到一起变成饺子的别名了。有人说扁食是馄饨,其实不然。馄饨皮儿薄,馅儿少,边沿铺撒着,下在鲜汤里,或者水煮以后捞出来再浇上鲜汤。一个挺有学问的朋友告诉我,严格讲,扁食就是带馄饨汤的水饺,但不是馄饨。而另一个更有学问的朋友说,扁食和饺子的包法也不同,饺子是捏,而扁食是攥,皮儿摊在手心,抹上馅,五指合拢一攥即成。
还记得当学生时读《水浒》,看到武松杀嫂那一节,武松问王婆:“你隔壁是谁?”王婆说:“他家是卖馉饳儿的。”一直闹不清这馉饳是啥东西,猜想过:八成就是水饺。直到有了网络,上网查,才大略明白它也是水饺的近亲,不过比水饺大得多(像小孩子拳头),包起来近似一个小葫芦,可以水煮,也可以用油炸。
扁食吃过,一次下乡在一个大队书记家里吃饭,他夫人就给我做了扁食,是胖胖的小饺子下在鲜美的紫菜汤里。当时我还挺纳闷:饺子还可以这样吃啊?觉得挺新鲜。至于馉饳那是不可能吃到的,因为它早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网上说那东西是用鲅鱼和韭菜作馅(根据出土文物判断),这又有点像蓬莱的鲅鱼饺子了,蓬莱鲅鱼饺子个头也挺大,大到一只手掌只能托一个,一个大磁盘(碟子)挤六个;不同的是蓬莱饺子是弯月形状而非葫芦形状,也没有油炸的。蓬莱鲅鱼饺子是一道胶东名吃。
水饺当然是开了锅以后下水煮,三开三点;其实饺子也可以煎,油煎、水煎,生煎、熟煎都可以。小时候的熟煎水饺记忆尤深。过年以后剩下的饺子多,在冷地儿放着,吃的时候拿出来入锅把几个面都煎到,金黄的颜色,入目便令人流出涎水;入口外焦里糯,又香又鲜。是可以待客的——大正月出门串亲戚接待客人是经常的事,熟煎水饺简单方便,也拿得出手;明明是没吃完剩下的,经过了煎这道手续,就变成了另一样美食。
随着生活的提高,饺子已经不再稀罕,早已进入了家常饭的系列,超市任何时候都可以买到,但人们还是喜欢时不时自家郑重地包上一顿;全家人一起动手,那是一种欢乐!超市买来的速冻饺,味道再好,也没有那种舌尖以外的温馨感觉,缺的就是那融融的氛围和情调。
饺子,里边包的不仅是美味,还有满满的亲情——无论是过年饺子还是平时伙食换花样,都是。
中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给饺子赋予了吉庆、团圆、和合的象征,愿这象征的意义永远延传下去!
本来就爱吃饺子,读了先生的文,对包裹着满满的亲情、象征着吉庆团圆与和合的饺子更喜爱了。
感谢先生的分享,受益匪浅!
俺不会评论,就就着江楼望雨老师的“碎了不能说碎了,要说挣了”说一个俺听到的笑话吧——
在赵格庄供销社(江楼望雨老师应该熟悉),有一年过年,经理和一个姓裴的职员留守值班。除夕夜,经理在炕上,职员在下饺子。经理为讨口气,问“挣了没有?”职员显摆他包饺子手艺好,一个不碎,一拍胸脯说:“放心吧经理,有俺老裴(赔)在,保证一个也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