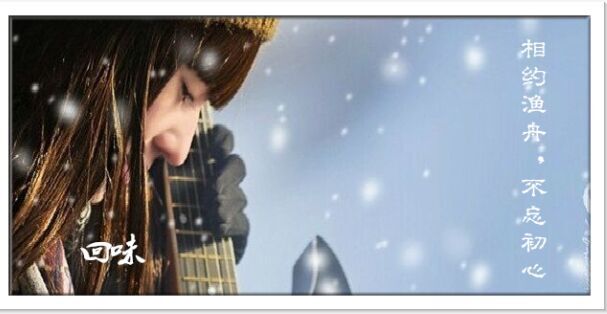【渔舟】见鲸(散文)
【渔舟】见鲸(散文)
![]()
早晨有雨。推窗看去,街上竟湿了一片。这场突如其来的雨让人无端烦闷,坐在桌边,欲下笔却又无词,想到最近的无事可做,便独自去了附近美术博物馆。想去看画展,已很久了。展览厅里,每一幅作品都在等候着它们的知音,然而人是这样少。三三两两的人群,像鼹鼠一样,自门厅来来去去,很快便鸦雀无声了。
美术博物馆不像历史博物馆那般,这里没有专门的讲解人员。就在一个刹那间,我的注意力被一幅油画深深吸引了,画布上游动着一头蓝色的鲸鱼。在它深蓝的眼睛里,在它光洁的额头上,仿佛涌动着无尽的空洞的海水。看尺幅,快有一面墙大小了吧。
冷光下,巨鲸与整个背景浑然一体,气势非凡。人站在画前,是那样渺小,如同置身海洋馆里。这是一头奋不顾身的大鱼,正在无边的大海里巡弋着。在它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深处的绝望。好像是命运所赐予我的,在离它一米开外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了巨鲸在歌唱。
曾经在《人与自然》栏目里,听赵忠祥老师解说过,鲸鱼不需要爱情,也不依靠同类,鲸鱼追求的是成为海洋之子。
没有比鲸鱼更为孤独的生物了,忍不住,掏出手机将这头巨鲸拍了下来,给美院的朋友老黄发了过去,问他,应该怎么欣赏油画。老黄倒是回复很快,说,每个画家表现手法都不一样,只能凭你自己的感觉。
凭借感觉,天马行空,老黄倒是挺懂我。
近年在一些展览上,油画尺寸越画越大,像这样挂在墙上的巨幅作品,给人的视觉冲击相当震撼,创作起来想必也耗费了不少时间。印象里,艺术家总以怪癖示人,是以总会被当做孩子对待。大部分艺术家都不修边幅,将身心融于作品,自然无暇关注外物,我突然理解了。梵高的脸上写满了破碎,所以创造了独特的星空,米勒的身体里流淌着痛苦,才有麦地里拾穗的女人。人们的眼光只会关注世俗的热点,正如谈论毕加索的时候,很多人却忽略了与毕加索齐名的达利。
很久,进来两位先生,手里都举着黑色的相机。拍照的声音,像玻璃一样滚落到地上。他们距离作品那样的遥远,不停调换着手上镜头,从入口走到出口,再折回来,如蜂采蜜,如蝶戏花,最后潮水一样从我身边流了过去。
他们窃窃私语着,讨论这幅画值多少钱,我的冥想被打断了。
书画以尺论价的惯例,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郑板桥。郑板桥爱画竹子,要价不菲,因此曾有诗曰:“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这尽管是雅事,但他们似乎把这里当做了画廊。见我独自站在巨鲸的油画前,便以为我也是这里面的参展者,主动介绍说他们是某报社的记者。对我这种一问一答才愿意开口的人,他们显然司空见惯了,一直引导着话题,强调最近结识了哪里哪里的名流,谁又因为他们的报导而有了影响力,其中有一位个子高的尤其推崇梁文道。尴尬的是,我对梁文道此人没有感觉。话不投机,很快就没有了聊下去的兴致,匆匆便告别了。其实怪不得他们,记者的天性,本就善于挖掘,偏偏我是个没有故事的人。
四周空旷得很,我戴着耳机,里面的广播正在放一首轻音乐,名字叫《LightsFrightenedTheCaptain》。这首曲子中途有一段录音,特别感染人心,异常缥缈,有金属的质感。站在走廊里,宛若置身于旧世纪的欧洲城堡。头脑一下被抽空了,无所思,无所忆,只能跟着音乐的节奏,在一幅幅油画面前久久地徘徊。直到走上了二楼,才发现这里的光线最是黯淡。美术博物馆里,常年都有四个展厅开放。就在我驻足观赏的时候,工作人员很细致地分出了三个板块。当然,还是女艺术家们的作品多一些,展厅犹如陈迹,安静地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负一层刚举行完揭幕仪式,正是热闹散去的时候。从架上绘画展厅里出来,走入到影像多媒体展厅,竟发觉此处更为幽深静谧了,而就在我身后,一眼望去,摆放着各种形态的雕塑,或俯身,或端坐,或站立,诺大的空间充满了艺术气息。每个板块,都有相对应的主题,架上绘画以谜语为题,影像多媒体以境象为题,雕塑装置以场域为题。
因为读过毕加索和达利传记的缘故,对身边这些抽象的东西,有着浓厚的兴趣,或多或少被我借鉴到了文学世界里。我曾在一篇小说里,写过一个女画家的故事,她的爱,她的恨,她对艺术的痴迷,最终却因为私生活的糜烂被逼得远走异国。在现实中,我对这些生活中的艺术家抱有崇高的敬意。面对这些美术作品,画中的一个人物,一缕阳光,一片星辰,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幻境里。
面对一尊沉默的雕塑,我会绕过题目上的标签,首先观想它们散发出来的气味:也许是在梅雨季节,那味道必定是带着潮湿;也许是在盛夏的时候,那味道一定沾染了香樟的气息;也许是在漫山红叶的秋天,那味道总有南国的忧郁和伤感;也许是在大雪纷飞的寒冬腊月,那味道夹杂着逃也逃不掉的苍白的底色。
美术馆的气氛有些压抑,大约与艺术有染,这里的时间流动得很慢。空气是凝滞的,颜料是凝滞的,画布是凝滞的,人也是凝滞的。乃至皲裂的树皮,生锈的铁丝,脱丝的棉麻……生活最隐秘的细节被一点点还原。记得托马斯·阿奎那说过一句话,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庄严,在实质上与慷慨一致,在形式上与勇敢一致。展厅的灯光愈来愈暗,衬托着亘古未有的安静与悲凉。我莫名地想到了尸体。想到了苦难。想到了乐极生悲。想到了须臾与幻灭。一个人的脑子里其实装不了多少事情,正如一个人生活的领域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辽阔。
从一些雕塑面前路过,走向另一个展厅,我渐渐体会到了策展者的心思。能让一个艺术的门外汉看得到毁灭,看得到重生,这或许就是情怀。展览的意义在于唤醒,在于重现。如同写作的意义在于表达,在于倾诉。站在青铜的马车下,我想起每日里庸俗的生活。当然,我也会回首这几年曾走过的路。所有人都在往前奔跑,我却一直停留在原地,一动也不曾动过。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重复昨日的生活,但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展览给别人看。公开的,肃穆的,没有居心的,像一篇未曾删改过的散文。
究竟,何为时间,何为生命,何为自然……停留在美术博物馆,一个下午的时间,让人觉得宁静,但并不能致远,只是暂时的,像一场幻觉,我永远无法真正脱离生活的漩涡。在这一场场的展览中,可能看不到技法的奥妙,也领悟不到色彩的匠心,我忽然觉得无比地疲惫,无比地沮丧,甚至懒得再去追究图景背后的故事。尽管,这一切都将会以艺术的名义,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或者说留存在文字里。
从梦想走向复兴之时,当经典回归现实之中,我学会了保持缄默,学会了平静地对待生活。四月很快就会过去。走回到街上,看着来往的男男女女,忽然感到一种巨大的孤独。是啊,不管你往前疾驰了多久,不管千里还是万里,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有终点的历程,就像哲学家费尔巴哈说的,死是生命最后的表露,也是完成。
一面在华灯初上的街头行走,一面想着文章的构思,这大概是我一天里最为放松的时刻。这座城市常年干燥,很少有雨,一到夏季阳光就会变得猛烈,所以每一条街道都植满了梧桐,洋槐。以前没去过南方的时候,非常向往南方的阔叶植物,半夜下雨时候能听到雨打芭蕉的声音,但后来去了南方后,却发现也不过如此,南方的雨水太过汹涌,就像人身体里的情欲一般,让我唯恐避之不及。
国内有三大公认的美学家,我喜欢读宗白华和朱光潜,年前和朋友逛街,在北京路上的联合书店特意买了朱先生的书,置于床头,睡前翻看一段,颇有自得之趣。朱光潜的话,对我影响很深,正如先生所说,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读《论语》的时候,记得孔夫子先前也说过类似的话语。人不可妄自尊大,却也用不着妄自菲薄,我的脑海里回荡着那幅巨鲸的身影,眼前不由地浮出了一片深邃的蓝色,仿佛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柳约的文字越来越有深度了,要读几遍,才敢写上几个字。你这小子,实在是学识渊博,姐姐跑断了腿,也是追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