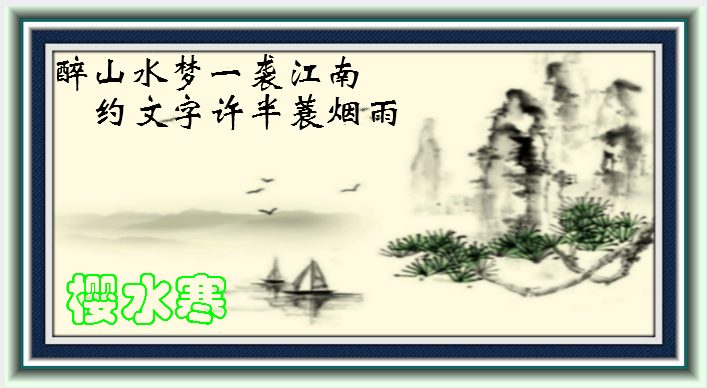【暗香】麦子熟了(散文)
【暗香】麦子熟了(散文)
又是一年芒种,农村该进入四夏大忙季节了。离开农村将近四十年了,很多农村的人和事都已淡忘,唯独对四夏大忙季节抢收麦子的印象颇深。这时的农村田间地头,该是一番独特的景象,挥汗如雨的收割写着这个时节特有的忙碌和躁动,喜悦和疲惫双双呈现在农家人那黝黑的脸上。
在儿时的印象中,麦收不仅意味着收获,也意味着那是一场沉重的攻坚。那时还是集体作业,没有农业机械化,收割主要靠人力。临近麦收,家家户户都忙碌地作着准备,多时不用锈迹斑斑的小尖(镰刀)在磨刀石上砥砺磨快,割麦,一把顺手而锋利的小尖,必不可少,可起事半功倍之效;准备好几根担绳(长约三米、一头紧系小枝桠为钩的麻绳)以便把割下的麦打捆,挑到打谷场;备好几只装麦子用的麻袋。集体方面也在作积极的准备,几位有经验的老农时时关注着麦子的成熟度,商议着收割的日期;打谷场上地势较高的地方整理好,作为堆放麦垛使用,防下雨时场地积水,浸泡麦子;未雨绸缪准备好遮雨用的帆布;脱粒机也加紧安装调试,谷场边用一根杆子高高挑起了太阳灯,准备开夜工用的。这些准备一般要几天,待万事俱备,就等开镰那一天。
麦收一定要天气好,而且最好有几天连续的好天气,若遇连续的阴雨天气,小麦容易倒伏、落粒、发芽、霉变。所以农民们必须抓住短暂的好天气,抢割、抢晒、抢脱粒,争分夺秒。麦子的收割也有讲究,烈日下;饱满的麦穗在天干物燥中一碰容易掉麦子,影响收成,必须利用大清早。趁着空气中有一定的湿度,麦穗沾露还软麦子不易掉落时抢割,因此,大清早是收割的最好时光。
收麦是个苦差使,太阳还没出,天还灰蒙蒙的。树上的鸟儿还在睡梦中,农民们就“开早战”下田抢割,穿上长裤长袖衣服或长裤短袖加套袖,把自己裸露的皮肤尽可能遮盖,防止皮肤被针尖似的麦芒刺痛刺伤,大热天的这么穿,不动也是一身汗啊。割麦时,弯腰,一手反向拢住麦杆,一手挥动小尖嚓嚓嚓斫断麦子根部,待胳膊底下一大拢时抱起码放在割光的麦地上,负责搬运的人用担绳捆好,或挑或抬,运往打谷场翻晒。饿了掏个麦面饼充饥,渴了田边木桶中喝碗醋冷水。割麦要十分地小心,一个走神或动作不协调就会割到自己的腿。千百次的接连不断的弯腰把人累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直不起腰,浑身如同散了架,有的干脆躺在了地头,大口大口地喘气。所穿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衣服上冒出了一圈圈白白的汗渍。割麦不仅苦累也很脏,麦上久积的灰尘和枯黄麦杆上的霉味受到震动混杂而起,直扑面门和鼻腔,把人搞得灰头土脸,也让人作呕难受。
或许是农忙,要干的活多,夏季的白天总是显得那么的漫长,忙碌的农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形象地称之谓早战、日战、夜战。“三战”几乎连轴转,中间只有短暂的吃饭休整。早战忙抢割,待太阳升高,就把剩余的留到明早再干,回家吃饭稍事休整,就进入日战。疲惫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可没法子,还得继续。一部分体力小的回到打谷场,翻晒麦捆,便于脱粒,另一部分去翻耕麦田,抢收蚕豆、抢种其它农作物,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凭经验把农忙的日子安排得非常的精细,井井有条。
晚上就抢脱粒,辛苦了一整天的农民们,匆匆回家吃口饭,就匆匆赶回打谷场,按照分工就位抢脱粒。五六个人抱麦放在脱粒机后的桌子上,桌子旁边的俩人把桌上的麦秸一大把一大把均匀地喂入机器,机前两则各站一人,一个用竹扒子,把脱粒机中吐出来的麦秸杆扒走,一个用铁锹把沉淀下来的麦子装入箩筐。空气中弥漫着抖乱的灰尘和麦香,灯光下望去烟雾笼罩有点朦胧,几只飞蛾穿过。这活同大清早的抢割相比已轻松了许多,农民们也明显活乏多了,一边干活,一边家长里短聊起了各种话题,肆意的笑声夹杂着机器的轰鸣声飘荡在打谷场的上空。虽然这活相对轻松了但也不能干久,站在脱粒机附近的人,受到机器噪音的强烈震撼,如暮鼓重锤在耳边震荡,两只耳朵嗡嗡作响,干一会儿,必须换一班人。这一晚注定很迟,脱粒完成称重看产量多少,留足集体以后,剩下的按照每家的口粮多少来分,并派专人送到每家每户,至此,抢脱粒的任务才算完成。
麦子到家,还算不上落袋为安;刚收的麦子比较湿润,水分多,长时间堆放不出风,麦子就会发酵变质,农家人都懂这个理,抢晒是唯一的办法。因此,家家门前搭起了长长的桁搁,放上芦苇帘子,再摊上芦扉,把麦子均匀地铺在上面,接受阳光的暴晒,这样晒,上下透风,干得快。每隔几个时辰,就用竹扒子推拉,把麦子上下翻面,使之均匀地晒出水分,正常天气下,四五天功夫就可以了。遇上天气突变,就赶紧回家,用塑料薄膜把整条桁盖住,雨过撩开再晒,六月的天多阵雨,这样的折腾要有几回。待用手一抓,麦子有嘎嘎的声响,或用牙齿轻嗑有嘎崩脆的感觉,那就干了。麦子的收藏也跟其它农作物不同,必须在烈日下进行,滚烫收藏才能防蛀防霉,藏得住、藏得久。顶着烈日,农家人用畚箕畚,一畚箕一畚箕地倒进半人高的大瓮或床柜中,至此,才是真正的颗粒归仓、落袋为安,可长舒一口气了。
麦子熟了,意味着忙碌和苦累,绝没有半点的李健《风吹麦浪》中的浪漫。或许是怕苦,或许是生活条件好了,都买大白米了,家乡的农户现在几乎不再种麦了,芒种时节回老家,再也不见了田间地头那气势磅礴的劳动激情和劳碌匆忙的生产节奏,也听不到了那高吭的劳动号子了,有的只是悠悠然和漫不经心的气氛。一切都变了,麦熟时分可能只有在上了年龄的人的记忆中还存在吧,年轻的都已不知道了,尽管在农村。
2019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