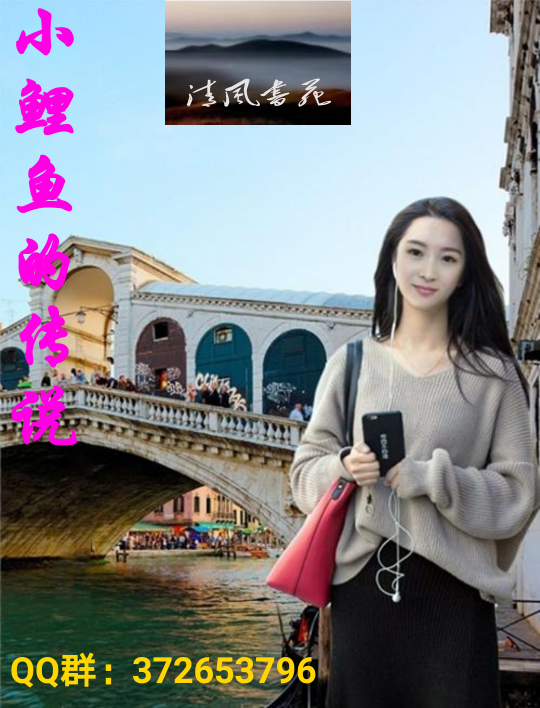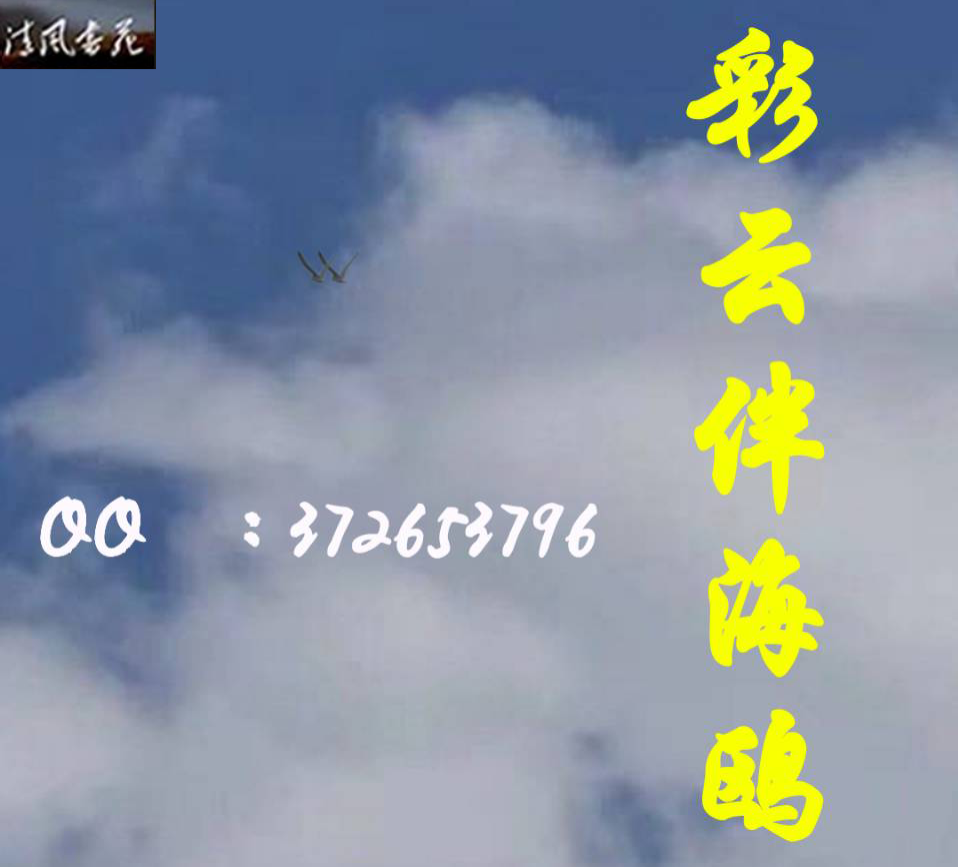【清风】又见稻飘香(散文)
【清风】又见稻飘香(散文)
![]()
暑假,不再属于我们。但风依然艳了花朵,也浓了树木。抽个空好好去拜访拜访效外的陌野。不看彩蝶花蕊上翩飞,不看池塘柳枝垂翠,只为看稻浪滚滚,看稻穗的金黄。
大清早,站在田埂上。一统天下的水稻不再是绿茵的色调。朝霞如一袭轻柔的婚纱萦绕在稻陌的上空。晨曦穿透这层薄薄的罗裙,明晃晃地撒在一层黄灿灿的稻穗上。微风轻拂,远处的的树叶轻轻的摇曳。活跃的小鸟在枝头清脆地鸣叫。低着头的稻穗缓唱轻吟着“刷刷”的曼妙调子。那是稻谷成熟喜悦的声音,也是农家丰收的天籁之音。依着晨风,挺着胸膛的稻叶舞动着穗尖上晶莹的露珠,齐刷刷的翩跹,婀娜的舞姿让人心醉。沉甸甸的稻穗摇曳着,摇曳着让人满怀欢喜的金色波浪。行走在原野里,湿润的空气里散发着一缕扑鼻而来微微的清香。闭上眼,听稻穗相互摩擦的声音,用力地吸吮在风中一缕接着一缕的气息。那香味,是沁进肺腑的幽香,如同远方袅袅炊烟下飘逸着的一种味道。什么味道呢?——那是米饭飘香的味道。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拥抱着大地抖动着金色灿灿的色彩。我不再看远方,只望故乡。搂着那缕稻谷的芬芳,仿佛又看见家乡人的微笑。
故乡,山多地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一分水养一分田,一分田就有农家的一分希望。垌中的,山麓里,小河的两旁。有水浇灌的每一寸土地都种水稻。
一滴汗水换来一朵稻花开!立春一过,乡亲父老就忙着犁坡耙田。也忙着把储藏一冬的谷种放在水缸里,用温暖的井水泡上,朝泡晚起,象呵护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着。约摸七八天,谷种长出了玉芽,才撒在秧地里。在乍暖还寒的春分前后,小秧长出四五片叶子,再把长好的小秧用锹铲起放进畚箕里,一担一担地送到水田里,躬着背,三五枝三五枝的一行行地插上。秧苗整整齐齐地立在平平整整的田野上,和水相交辉映。水里有空中布谷鸟飞过的影子,有天空的影子,有山岭树木的影子,也有家乡人忙碌的影子!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儿时熟稔诗词中农民的艰辛,那是诗人画卷,但不走进田间,那知道个中腰酸背痛的滋味?浇灌除草防害虫追肥。那个环节都少不了。
晨露,阳光还有月华,不经意的演绎着世间所有生命的历程。直到过了夏至,稻禾绿成不分彼此,绿成禾叶的相互拥挤。在村庄里荔枝树龙眼树的嫩绿长成苍翠的叶子,树上的细碎碎的小白花与淡黄的花簇悄悄收敛了热烈的时候。稻田的稻禾才完成了人们提供给它的生命能量,在禾胎分娩出来洁白洁白的、细细碎碎的小白花拥簇成穗,粒粒成熟。
“小暑小割,大暑大割。”这是我们那里的农家谚语。收割,是农民欢喜的日子,也是最苦的日子。现在,机器的劳作已经代替了几千年的刀耕火种的艰辛。但是,儿时乡亲父老抢收的情境如同我离乡的脚步,渐行渐远,却依然历历在目。
稀疏的星光还在闪耀,蟋蟀还在做梦,蝈蝈还在酣睡,小路边小草上的露珠就被行人匆匆的脚步碰落。田头间,不时有人影晃动。没有消闲半刻,弯下腰挥开镰刀,把稻穗一把搂进怀里,“刷刷”地收割起来。随后把割下的稻穗一把把整齐地摆好进畚箕里,用肩膀一担一担地运回村子里的晒场。
晌午,日头吐出毒辣的火舌,滚烫的气温烧烤着大地,阵阵的热风暗涌。雨燕不断地在田野的上空“天落水,天落水”地高鸣,蝉虫一声高一声“知了知了”地凑着热闹。声声急促,崔促着趁着赶晴农家人快快收割的步伐。
暑热的高温更考验人的意志。躬身在田间收割的人儿,汗水顺着笠帽的带子流在被阳光烤得通红的脸颊上。渗进胸膛,湿透了全身。用手臂上的袖子狠狠一擦,不一会儿豆粒的汗珠又挂上额头。汇在眉头,结滴成串,“叭哒叭哒”地落在稻田里。挑禾把的人儿的背后,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盐白盐白,腾发着热辣的蒸气。每个人都背着一幅不同形状的地图。天地玄黄,阳光不留置半点缝隙,大地找不到一处阴凉。人在移动,亮丽的地图也在蠕游。
傍晚时分,待太阳又回到了昨晚的山峰。人们才回到晒场,把收割放在晒场上的稻穗用禾杈均匀地倒乱,圆圆的一堂。男人牵着牛绳,大声吆喝。牛儿哞地一声,拉动串联在牛肩上特制的扁担,石滚吱呱吱呱地一圈圈地碾压着稻穗,硬生生的稻穗经过前三轮后三轮的碾滚,谷子脱落在被碾滚柔软的稻杆里。脱粒之后,还要倒翻开稻杆。把稻谷收起,放进风车里扬开细碎的稻叶。收好稻谷,转移晒场的稻杆。往往是月光偷偷淹没了墙根的时分。
要是遇上阴雨天的来临,就更苦了。因为一场的风雨都会夺去农民一春付出的汗水。风会打倒成熟了稻禾,水也会泡臭倒在水田的稻谷。时间就是农民的口粮,农民都和时间赛跑。记得那个时候,为了抢割,人们就把有罩子的马灯,三角灯点上,挂在杆子上立在水田的中央,一盏,两盏地亮起来。朦胧的灯光,星星点点撒在稻禾上,点缀着人们忙碌的身影。
那些年,走到田间,到处可以看见人们收割稻谷的忙碌情景。孩提时代的我们,帮不上忙。隐现在记忆墙里的是,就是像一群撒在河里的鸭子,不再去理睬树上鸣叫的蝉,也不再去攀石崖掏鸟窝。就在收割过后的田野上逛荡。瞅见稻茬里有遗留的一线半颗稻穗,就放开脚步,一边体验着百米冲刺的感觉,一边向稻穗飞去。七月的流火,把我们的皮肤烤得乌黑发亮,黑不溜秋。没有现在的小孩白白净净,水灵可爱,但绝对的健康,绝对不缺钙。
尽管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农村。但乡亲父老用木头做成的禾叉抖动着稻杆,那优美的动作如大型“歌舞升平”舞蹈赏娴熟的姿态,一直绕系在心间。藏匿不住的稻谷落在地堂上发出黄色的光晕,毫不吝惜地挥耀着它剔透层叠交缠的色彩。更是让人在梦里也挥之不去的缭绕。“急水冲沙粗在后,劲风吹谷秕先飞。”父亲边摇着风车,边念着那时候我不知所云诗句。我蹲在风车边,双手挡着风车流口的谷子玩,缠着他解释。父亲拍了拍了拍我的小手,露出淳朴的笑容,指指坐在屋檐下的奶奶。
夏秋之交,乡村白天的太阳是明亮的,晚上月色也是美好迷人的,一颗树,一扇窗,一条小河,甚至一缕拂过脸颊的清风,都是那么的清晰。旧屋的檐下,挂着一小撮一小撮在稻田拾遗回来的稻穗,如风铃般摆动。奶奶端着簸箕,揶挪着晾干了的稻穗,双手抱起一捧谷子,用嘴一吹,秕谷纷纷扬扬的飘出。我一屁股坐在簸箕里,非要奶奶解释父亲念的诗句。母亲嗔怒,奶奶却不生气:话说以前有个聪明的学子,因农忙而担误赴考的一些时间,父亲就为了让更快赶路,父亲用肩驮着他涉水赴山来到考场,但考场已经闭门静考。他们急切要求考官亮绿灯,让这位学子进考场。考官见他父子俩的样子,调侃他父子俩,说道“令父作马”,那位学子脱口而出“望子成龙。”考官感觉他到聪明过人,便出了一个条件,前提是要学子出一首工整的对联方能放行。他想到河中的沙和风车里的谷子,脑子机灵一转,就有了“急水冲沙粗在后,劲风吹谷秕先飞。”。故事中的那个学子后来高中状元,就有了这个典故。
我也是农忙过后伏在父亲的后背走出了农村。我把父亲当马骑,可我违背了父亲望子龙的心愿。因为我一直依恋,依恋母亲把淘洗过后的新米放进沙锅里,火苗舔锅底。锅子盖上的乳白的气雾绕着炊烟吐出香喷喷的味道。还有坐在奶奶的旧旧簸箕里,有如乳汁般甜蜜的故事。
走在异乡里,我不止一次哭闹着,要回家。父亲却对我说,他乡也可以是故乡。可是,父亲却欺骗了我。看到稻浪滚滚,看到稻穗的金黄。一种思乡的惆怅穿透过心脏,我无法掩饰自已的忧伤。如果可以不必放逐他乡,我甘愿,我零乱的脚步从没有走远,一直踉跄在家门口的那条小田埂上徘徊着。因为无论我们走多远,我们都是故乡的孩子。故乡有母亲生火做饭的汽味,也有奶奶的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