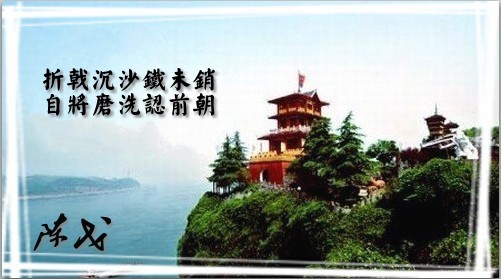【江南】灯笼会 澎湖湾(散文)
【江南】灯笼会 澎湖湾(散文)
![]()
灯笼会,灯笼会,灯笼亮了长一岁;
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
伴随着这首童谣和我一起成长的,还有那首叫做《外婆的澎湖湾》的歌曲。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幸福的事,而那个新的生命,也随着一声声响亮的啼哭开始了新的生命旅程,有欢笑也有悲伤,有坎坷也有坦途。
年迈的外婆便迈动着小脚为这个小生命忙活开了,端午节送粽子,重阳节送柿子,特别是正月送灯笼。每个孩子在正月十一晚上要挑上外婆送的灯笼,一直要挑到12岁。这是我们这里的年俗,也是上一辈人对孩子的呵护和祝福。小时候问母亲为什么非要挑到12岁,母亲就说:因为过了12岁啊,你们就变得强壮了,健康了,再不需要神的庇护了。
灯笼会,是新年的另一种味道,是孩子们的天下。
我小时候,孩子多,一到晚上,满村满巷里都会亮起红红的灯笼,响彻着我们无拘无束的欢笑。
一两岁的孩子,是不会自个挑灯笼的,一定得大人帮着扶着。抱着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会聚在一堆,谈笑着,憧憬着美好的明天,互相称赞着对方的孩子,一团祥和之气。大人也会帮着孩子把手里的灯笼摇来摇去,一边哼唱着那首《灯笼会》的童谣,一边和对方的孩子的灯笼碰来碰去。要是不小心灯笼里的蜡烛倒了,灯笼就会烧着。孩子看着灯笼着火了,有的会吓得哭,有的会开心得乐。大人会哄哭着的孩子说:灯笼着火了好,我们的蛋蛋娃会长得快,咱家来年也鸿运亨通呢。
三四岁的孩子,就会自个挑着灯笼满巷子里窜了,大人跟在后边愣是追不上。一边大声吟唱着那首耳熟能详的童谣,一边和同龄的孩子碰着手里的灯笼。要是灯笼着火了,就会追着没着火的灯笼碰,还一个劲地说:我家还有呢,烧完了我再挑个新的。外婆说,送的灯笼要挑完呢,不能给来年剩。这样一来,怕灯笼着火的小朋友不跑了,回过头,会故意让自己的灯笼着起火来,还一个劲地说:我也有呢,一晚上烧两个也挑不完。
这会,大一点的孩子会赶过来凑热闹。他们虽然还没到十二岁,但不挑了,觉得自己长大了,挑个灯笼太小儿科。他们会让外婆送灯笼的时候买一些眼前花。点着了,手里就燃放着一串烟花,提在手里轮来轮去,眼前花就一边“滋滋滋”响着,变幻着不同的图案,煞是好看。当然,胆小一点的,会躲得远远的。那些男生却不省事,非得追着躲来躲去的孩子,直到把他们吓哭,或者跑回家才满意。
再大一些,我们也就不挑灯笼了,外婆却还是照样送,因为她的外孙孙还没到十二周岁呢。灯笼会,成了另外一帮孩子的天下,但我们怎能闲着呢?依旧是满巷子里窜,做一些让大人厌烦的事,捣着自己执着荒唐的蛋,肆无忌惮地念着那首童谣,将栖息在树上的鸟雀都惊得到处乱窜。
灯笼一直要挑到正月十五的晚上,但灯笼会还没有结束。正月十六晚上,要是有年前结婚的新婚夫妇,便会在门上挂两个大灯笼。那是我们半大的孩子最向往最憧憬的时刻,那高高悬挂在门两侧的灯笼,是另一种形式的灯笼会,家里挂了大红灯笼的哥哥们,从此就有了一个家,村里也多了一个漂亮的新娘。帅气的新郎,漂亮的新娘,总是穿着时髦的衣服,甜甜蜜蜜地走过大街小巷。我们便会在老远喊:新媳妇,新媳妇,羞羞羞!当了新郎官的哥哥们或叔叔们也不闹,指着我们说:甭让我逮着你们,让你妈给你找个媳妇,看你们还皮不?
村里有一些能说会道的,爱笑爱热闹的妇女,会在正月十六晚上,给新婚夫妇去“送娃”。就是做一个假娃娃,去新婚夫妇的家里耍闹一番,也是送去好运,希望来年新婚夫妇能早生贵子。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会跟在这些送娃的妇女后面,一家一家看热闹,混些瓜子和水果糖吃。听那些妇女们说一些玩笑话,俏皮话,看得乐不可支。晚上一个人躺在婆烧得滚烫的土炕上,就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长大,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那些懵懂而甜蜜的滋味,让我们觉得时间是如此漫长,时光却如此静好。
慢慢地,我们长大了,再唱起《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时,莫名的有些许伤感。也许是小时候,经常去外婆家,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那时,外婆总是把好吃的留给外孙。在外婆家里,总是能肆意地玩闹,还有表哥表姐们,总是那么亲昵无间。也许是因为长大了,上学了,去外婆家少了,而外婆也渐渐老了,走不动了。真的是没有椰林缀斜阳,只剩下一片海蓝蓝了。外婆也不能再挽着我们的手,踩着夕阳的余晖,走向那个暖暖的澎湖湾了。记忆里,只剩下遥远的沙滩,和那首遥远的童谣。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小时候的灯笼会不再那么热闹,那些红红的纸灯笼也变成了电灯笼,小孩子们挑着,灯笼里还播放着动听的儿歌,再碰也不会着火了。
年,还是那么的热闹,繁花似锦,吉祥如意。我们在年的祝福声中,守望着亲情,也珍惜着友情,杯盏交错,欢声笑语里,多想再喊一喊,吼一吼:
灯笼会,灯笼会,灯笼亮了长一岁;
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
也多想再唱一唱那首《外婆的澎湖湾》啊!可是每每开口,便不由泪眼婆娑。如今,外婆在哪儿呢?阳光里,沙滩上,还是海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