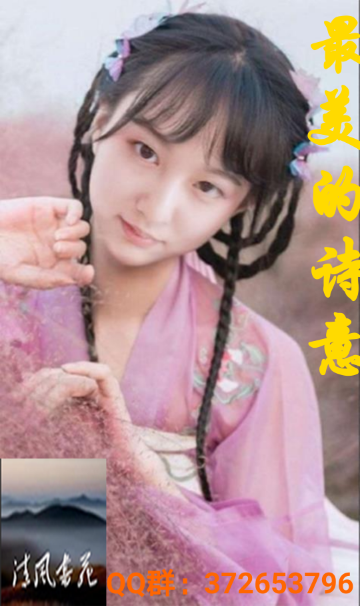【柳岸•韵】黄土哲学(散文)
【柳岸•韵】黄土哲学(散文)
![]()
一
哲学是抽象的,我不想用抽象来诠释我钟情的黄土地,黄土地上的人和事,自然会告诉我们什么是“黄土哲学”。
提起黄土地,首先充盈于脑海中的便是,如微风吹过后的海面上那种泛起的一道道波浪般的黄山,黄山承载着黄土,黄土裹着连绵不绝的黄山,这便是我最初对于黄土地的印象。在我的概念中,土,必须是黄色的,而如长白山下的黑土,长江岸边的沙土则都算不上真正的土,至少,在我的定义中是这样的,也许这种概念,算得上是一种偏见,算得上是一种执拗,更算得上是一种狭隘。事到如今虽然我一年中或许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是将双脚踩在真正的黄土之上的,但是这种称得上偏颇的定义,却从来不曾改变,我想,这一点可能就像我不论离家多远,多久,都能随时随地说出地地道道的陕秦方言一样,发自于骨头,源自于心底。
记得小时候不知道从几岁开始,我便莫名其妙地患上了一种怪病,这种怪病只要遇到天气冷热交替,或者出汗后突然进屋,便会马上满身长满红色疙瘩,奇痒无比,痛苦难耐。家里老人说这叫“风屎”,长大之后,准确讲是直到我有了孩子后,才知道那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荨麻疹”。风屎搞得我总是整夜整日间地抓挠,甚至扣破、流血更是司空见惯,虽然在这期间,父母带我看过医生、吃过洋药,但是都只是临时见效,事后照旧复发,严重的时候甚至一觉起来,两只眼睛都肿得无法睁开,后来有人给父亲建议,说用啃过的西瓜皮来回擦拭患处,便可削除,于是在那年的夏天,全家人吃完的西瓜皮都被我据为己有,整日捏着瓜皮在身上或者脸上蹭,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反而搞得浑身黏糊糊得,西北风吹过后,带起来的尘土全被黏在了皮肤上,整个人便瞬间于黄山黄土浑然一体,不分彼此,那状态真的很是滑稽。直到大概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突然有好心的村民给了母亲一个良方,而这次的民间方子,却意外地根除了缠了我好多年的风屎困扰。这个偏方,便是使用猪圈里的黄土(最好是猪窝里被踩得细碎的那种)为引子,抓起来捏碎,抹到患病处,只要起了疙瘩就去抹,如此反复,便可达到治疗的作用,就这么简单。站在医学的角度,我不知道这个方子有何科学依据,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后来事实证明它却实实在在地治好了我的风屎,至今三十年过去了,被猪圈里的黄土治愈的风屎,一次也没有再复发过。
其实后来我偶尔会琢磨,也许这个方子,或者诸如此类看似土得不能再土的“黄土”方子,它不见得对任何人有效,至少我认为对南方人肯定不会有效果,而我这个个人观点的依据,仅仅是那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论点,我出生在黄土垒砌的土炕上,自小用黄土块擦屁股,用细黄土止血,这种药理对于黄土地上生出的人而言,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而诸如我个人的这种对黄土的奇怪用途,在黄土高原上还有很多,生在黄土地上的人,黄土对于他们来说,竟然有着无时不刻,无所不在,贯穿一生的联系。
二
在以前医学不够发达,而黄土高原的医疗又基本是零的时代,黄土地上的婴儿离开母亲的身体后,铺在身下的第一件“毯子”,便是厚厚一层用擀面杖擀得绵软无比的干燥黄土。婴儿落地,带着母亲的血水一起,置身于铺在母亲身下的一片黄土之上,转眼之间,干燥绵软的黄土便将血水以及婴儿身体上的液体吸吮干净,而吸满婴儿和母体血水和体液的黄土,随之被陪在身旁的家人用麦秸清除,泼洒于门前的菜园里,西北风吹过,一切再一次与大地浑然一体。而被黄土接待后的婴儿,便从此与黄土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婴幼时尿炕后,黄土吸吮竹席,然后用湿抹布擦拭,随之便马上可以被火炕烘干,不会留下任何异味;大小便后,黄土块儿代替而今的卫生纸来清洁,干燥且自带消毒功能,且取之于脚下,归还与脚下;嬉戏打闹擦破膝盖,捏碎的黄土止血也是最好的,最便利的方法;上火磕碰后鼻血直流的时候,每个母亲都会在墙角捡一块黄土块,夹在耳根,仰头几秒钟,鼻血竟然都会神奇般停流。黄土地上生长的百姓们以口口相传,以身做例的方式,一代代,将这些神奇的“土”味十足的方子传了下来,在很大程度上,黄土成了并至今依旧是黄土地上百姓们最廉价而最有效的药物。
世代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因黄土而结缘红尘,恰如前文那样用黄土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而之后便又以黄土为伴奔走红尘,或是一季风调雨顺的岁月,或是一度缺风少雨的年岁,黄土都以一种笃定而近似于执拗的姿态,孤傲地立在黄土汉子与姑娘的身前,为其拓路送其前程,或为其立墙为其起灶。挖起脚下的黄土做料,不添加一滴外来的水,不使用一粒细沙,纯纯粹粹的、湿柔的黄土一层一层叠加,带着黄土汉子挥舞石杵的汗水一起,夯成一座方方正正的三尺高墙,再用黄土打成的土坯垒砌两座厚实而温暖的房屋,至此,黄土从接生一位婴儿开始,算是彻彻底底看着他们成家立业了,并将用这座黄土夯打的“城堡”作为基地,陪伴着黄土人的一生。而黄土地上的人们,依旧用黄土垒砌灶台火炕,在黄土里春种秋收,喝黄土下渗出的泉水,吃黄土里长出的庄稼,并以如此近乎于自给自足般的日月中,酣然于悠悠岁月,把日子过成了黄土般平凡,把头发染成了黄土一样荒寂,待阳数末了,又以一身崭新的衣服裹着,躺进一方三尺黄土中,从此世事喧嚣皆了然,红尘百般一黄土。
三
黄土地在祖国的地图上体现出来的样子总是纵横交错、支离破碎。我总是喜欢在偶尔消闲的时候,把属于黄土地的那一块地图使劲放大去看,也许我是在尝试看看能否在某一个沟壑里,找到我曾经牧羊的那片林子,或者我们家的那块儿草木茂盛的祖坟,然而也许是我过于焦急,也许是黄土地过于谦逊,我总是很难找到它们,而每每当我踏上那一片生我、并养活了我二十多年的黄土地的时候,总会莫名其妙地生出许多久违而亲切感觉,我权且称之为“安全感”吧,这种感觉陪着我度过了哭鼻子尿炕的那些孩童岁月,更伴着我走过了漫漫求学生涯的十多年时光,而今它正在一如当初完全一样的步调,陪伴着那些喊我叔叔的小孩儿,那种沉默的样子像一位蹲在村头儿的树根上抽烟的老人。
我不喜欢别人提到黄土地,便提到“千沟万壑”这个词儿,在我的理解中,说沟壑者,本身是带有贬义情感的,而沟壑本身也是粗陋的,而如若没有在黄土地上生活过,是无法真正去理解黄土地的形象与精神的,站在黄土崖下随便一声嘶吼,黄土崖给出的那种荡气回肠的回音,定然会让你对它心生几许敬畏,更何况,这里的每一粒黄土,也许都是曾经某一位“接生婆”,是今天某一位游离四海的苍鹰,儿时的保姆。如果将一方黄土与黄土之上的生灵,黄土之下的先辈们联系,这方寂静而沉默的黄土,则变得无不令我倍感敬畏,近乎于顶礼。
世代生存于黄土地上的人们,对黄土的理解,远远超出了他们本身所具备的知识范畴,而他们对黄土以及黄土地的依赖,更像是学步孩童对母亲的依赖,而之所以有如此深邃的理解,有如此百般的依赖,才有了他们、或者我们对黄土地以及黄土所怀有的对于任何黄土地之外的人所永远无法理解的敬畏之心。对于黄土地以及对黄土的理解和依赖,我认为这是一种类似于最朴素的百姓哲学,也许可称之为黄土哲学。
生于黄土、长于黄土、与黄土一样的肤色,是一种融合的态度。守着世代不变的黄土地,以世代不变的黄土地,陪伴一代又一代黄土地上长大的孩子走向黄河的两岸、大江的南北,这形象,像极了一位“土”味儿十足的农村老父,守着黄土夯起的院子,望着远处也许在东南某地的娃娃。
对于黄土以及黄土地的理解,相信我这点文字完全不足触及其皮毛,然而,至少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黄土地和黄土地上的百姓们,对黄土哲学的这门理论的理解与敬畏,远远超过了我十年寒窗所学到的任何一门技术。
再一次踏上黄土地,我以一个黄土地上长大的孩子身份,五体投地的姿势伏于其上,我触到了黄土地温热的黄土,闻到了黄土袅袅然蔓延于鼻尖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