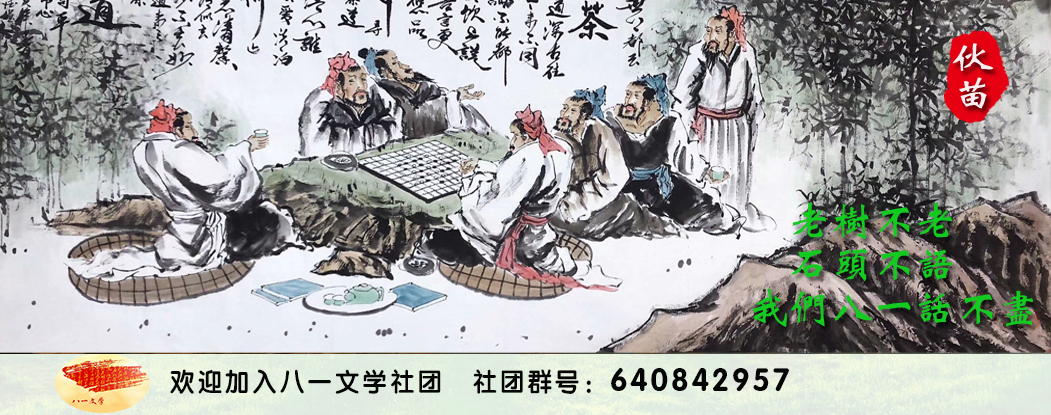【八一】记忆中的老屋(散文·家园)
【八一】记忆中的老屋(散文·家园)
![]() 在我的书柜中,保存着一块青砖,这便是我心中的老屋了。
在我的书柜中,保存着一块青砖,这便是我心中的老屋了。
封存了五十多年的记忆,零零散散的;好多次,我凝视着这块青砖,努力收拾起记忆的碎片,但久久不敢落笔,老屋在哪儿呢?
我竭尽所能,能够回忆起来的,是我三岁以后的一些记忆,老屋很暗,是一栋黑漆漆的三开间旧房子。
在我印象中,那老屋,我一共去过四趟,可奶奶告诉我,应该是五趟。在我刚满月的时候,奶奶带着我父母和我,是去过一趟的。
解放前,我家在乡下也算是殷实人家,太爷爷、爷爷是读书人;太爷爷教过私塾,爷爷在上海的大洋行里做事,奶奶守着祖上传下来的老屋,还有几亩薄地,日子算是比较清闲的。
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竭尽掠夺之能事,我家也不能幸免,好多字画、古董被日本兵抢了去,爷爷在上海也站不住脚,回乡下避风头;不久,太爷爷和爷爷相继过世,家道就中落了。
奶奶带着我父亲,守着这份家业,日子虽然清苦,但还是秉承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遗风,送父亲去省城的新学堂念书。这在当时的乡下,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了。
四九年解放时,父亲在学堂里参加了革命,后来回到家乡,就在县政府做事。
土改的时候,我家因为有一栋老屋,还有几亩薄地,因此阶级成分是富农,田地分掉了,就留下一栋老屋。
我父母婚后,在县城的横头街分到了房子,奶奶就一个人住在乡下的老屋里。
一九五七年,因为父亲有点文化,被政府抽调去江苏筹办化工厂,奶奶就从乡下搬过来,和媳妇一起住,这老屋就这么一直空着。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是比较陌生的,一年也就回来两次,一次是探亲假,十五天左右;一次是春节,七八天左右。
听奶奶说,父母婚后,好长时间都没有怀上孩子,奶奶是真着急啊,就偷偷地回了一趟老屋,偷偷地拜了祖宗。
还真的灵念,后来我就出生了,那年是一九六六年。
我满月那天,奶奶执意带着父母和我,去了一趟老屋,偷偷拜祭祖宗,感谢祖宗庇佑,为老钱家延续了一脉香火。这当然是奶奶后来唠唠叨叨告诉我的,那时我还根本不记事呢。
记不太真切了,应该是六九年的一个夏天吧,我叫名四岁;那天来了好多人,清一色的绿军装,大人们称他们为红卫兵,是来破四旧的,乒乒乓乓把隔壁祝家的花瓶、有点图案的餐具砸个粉碎,还没收了一个存放金条、银元和首饰的小盒子。
出大事了啊,祝家爷爷和他儿子,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了,游完街,还要到居委会挨批斗。
我记得,我奶奶抱着我,也得去开批斗会,小孩子哪懂这些事,我还举起小手,咿咿呀呀喊口号呢。
第二天,奶奶带着我去了一趟老屋,这是我对老屋的第一次记忆。
老屋白墙黑瓦,那白墙根下,布满了青苔,虽说是白墙,但现在想来,由于年代久远,那墙其实是偏灰色的;老屋正面是暗红色的木质门面,朱红色的双开大门在正中间,两边的窗户不大,但显得精致,和顶上的屋檐都好像是雕了一些图案的,让人一看便知道,是当年乡下富裕人家的房子。
门前的一棵老榆树,我的记忆尤其深刻,很粗,很大,三个人合抱,不一定抱得过来。因为树下有一口老井,所以奶奶不让我靠近,而是直接进了老屋。
堂屋正中是一张八仙桌,四条长条凳;对面墙下正中,有一个香案,应该是原来祭拜先祖的所在,现在香案上面墙上贴的,是一幅毛主席画像;厅堂的左右各有一对太师椅,中间配有茶几,所有家具都是暗红色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上好的红木家具。
在厅堂东边,是原来爷爷奶奶的大房间,梳妆台、衣柜、樟木箱等,和厅堂的家具陈式差不多,只有那张大床和马桶箱是大红色的,特别耀眼;那张大床,就跟现在旅游时参观的清代家具一般模样,三面是雕有动物、花卉的床栏,床顶的装饰也极为考究。
我后来才知道,这张床在当年就很值钱了,那三面床栏上的动物、花卉,其中的十八处,是玉石做成的,还镶了金边,也就是现在所讲的金镶玉工艺了。我当时实在太小,没看得那么仔细。
奶奶进到房间,就翻箱倒柜地找出一些东西,有花瓶、字画,还有许多画了花鸟山水的折扇,统统搬到厅堂间里;然后又从西边原来我父亲的小房间里、灶间里寻出些瓶瓶罐罐,碗盏碟子。
奶奶当时咬牙切齿的,用一根擀面杖,把花瓶、碗碟敲个粉碎,我觉得那叮叮咚咚的声音真是好听,也就帮着奶奶摔碎了三个小碟子。
奶奶把敲碎的瓷片装进一个量米的布袋子里,又把那些字画、折扇堆在了大门口的老榆树下,点上一把火烧了。在回来的半路上,奶奶把布袋子扔进了一条不知名的河里。
我当时就觉得好玩,没有过多的想法。后来才知道,奶奶是见到红卫兵破四旧,怕了;怕这些“四旧”会伤害到家人,怕也会被捉了去游街、挨批斗;为了家里人免遭劫难,奶奶就把这些害人的东西都处理掉了。
直到九十年代末,字画、瓷器开始值钱了,父亲才跟我说起,太爷爷的爷爷是清代有点名头的画家,喜欢搞些收藏,尤其扇面画得十分出色,当年老祖宗画的折扇,三两银子一把,都很难买到。怪不得奶奶烧掉的字画中,有那么多的折扇啊。
现在想来真是肉痛,一把火,一根擀面杖,奶奶连一点念想都没给后辈留下啊。
我六岁那年,也是一个夏天,雷阵雨特别多,乡下的远亲带话过来,说是四奶奶家的房子塌了,还好没有伤到人。
四奶奶是奶奶的堂嫂,比奶奶大不了几岁。奶奶心善,想着乡下的老屋空着也是空着,不如先让四奶奶家暂住,房子修好前,总要有个住的地方的。
奶奶带着我去乡下,四奶奶家遭了难,总要去看望一下的。
那时到乡下,全靠两条腿走路,也就十几里地,奶奶也抱不动我,只好自己走。大概走了两个多小时,我腿实在酸的不行,就赖在地上不走了;奶奶说:“小祖宗,快点起来,还有两里地就到了,都过了晌午了啊。”
我是又累又渴,还觉得饥肠辘辘的,就索性闹起了小性子,早知道这么受罪,打死我也不会跟着来啊。
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天空一大片乌云推了过来,一时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江南夏季的雷阵雨就是这么突如其来,怪不得四奶奶家的房子会塌了啊。
空阔的乡间小道,布满泥泞,没有一处可以躲雨的地方,我是顾不得使小性子了,急忙跟在奶奶后面往前赶;伞都没有一把,不到一分钟,奶奶和我都变成落汤鸡了啊。
远远地,终于可看到老屋的屋檐了,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老屋跑去。
突然,一条硕大的黑狗蹿了出来,冲着我狂吠不止,我赶紧逃到了奶奶身后,浑身止不住地打颤。
太可怕了,这条恶狗,对于才六岁的我来说,无疑是一头大灰熊啊。
奶奶挡在前面保护我,其实她也是挺害怕的,就这么跟这条狗对峙着;狗一停不停地狂叫,把我们逼到了一处无路可逃的秧田里。
我哇哇大哭,居然会高声喊起了“救命”,哈哈,看来怕死确实是一个人的天性了。
真是到了崩溃边缘了啊,四奶奶闻声赶了过来,就这么一吆喝,那条黑狗就钻进芦苇丛中跑掉了。
来到老屋,四奶奶不停地对奶奶说些恭维话,还说差不多半年,这坍塌的房子该会修好的。
奶奶笑了:“我又不会来跟你要房租,你放心住着就是了,赶紧去帮我寻些干衣裳来。”
原来四奶奶心里还是有点小九九的,担心奶奶这次来,会不会向她收房租,现在有了答案,就欢天喜地地去寻衣裳,然后下厨房为我们准备中饭去了。
老屋的陈式没有多大变化,就是厅堂间里堆了一些从四奶奶家搬过来的杂物,看起来有点凌乱。我趴在小窗口,看着屋檐上挂下来雨线,想着自己的小心事:等下回去,那条该死的恶狗还会不会出现。
说是中饭,其实是两道点心,一人一碗酱油汤的肉馅馄饨,外加一盘南瓜陷的蒸馄饨,这或许是那个年代乡下招待贵客最高的礼仪了。
那肉馅馄饨真鲜,那南瓜馄饨真香。直到现在,我还总以为馄饨实在是世界上最值得回味的美食了;当然,狗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
四奶奶是几时从老屋搬出去的,我真的不知道,大人们没跟我说起过。
奶奶亲手毁掉了家中的四旧,也没能挡住家里人遭难的命运,我八岁那年,刚上一年级,已经有点懂事。断断续续地听到奶奶和母亲的窃窃交谈,得知父亲被划成了右派,下放到一个农场接受改造,两年来没回过一次家,吃苦头不说,家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断掉了,这日子过得好苦。
母亲思念父亲,积忧成疾,住进了医院;奶奶则尽力维持着家庭的生计。
屋漏偏逢连夜雨,乡下的阿刚伯带话过来,说是老屋一直空着没人住,家里不知什么时候遭窃了。
奶奶带着我风风火火赶到老屋,真是家徒四壁了啊。厅堂间里,八仙桌、香案、太师椅、茶几都不见了,就留下四条长条凳;奶奶的大房间里,也几乎搬了个精光,那个价值不菲的大床,散了架堆在地上,床栏上的十八块金镶玉被撬走了。许是那床实在太大、太沉,窃贼搬不动,只好破坏性地盗走了那些玉片。
奶奶好生心疼,这老屋是实在照顾不到了;当时父亲回不了家,母亲躺在医院的床上,家里上上下下全靠奶奶操持,哪里还有精力管这档子事啊,何况,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啊。
奶奶心里想着,照这样下去,老屋什么时候被人扒掉卖了都不知道啊,干脆处理掉算了,家里正缺钱呢,也好贴补点家用。
奶奶委托阿刚伯寻找买家,家里遭窃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唉,那个乱哄哄的年代,谁知道这些祖传的红木家具,若干年后的今天,会价值连城啊;就这么被偷走了,案都没报一个,也不晓得调查一下,算是成了千古之谜了啊。
邻村的小学要盖一个食堂,缺少建材,听说有人要拆了旧房子来卖,就跟阿刚伯联系上了,经过讨价还价,以五百二十元成交。
拆房前一天,奶奶带着我,最后一次去了老屋。
奶奶在朱红色的大门前拜了几拜,点上三炷香,让我代替父亲在门前磕了三个响头,说是败了祖上家业,对不起祖宗。那年我刚九岁吧,似懂非懂的,按奶奶的吩咐,照做便是。
听说也就两天时间,老屋就被拆掉了。
靠着那笔卖房子的钱,奶奶硬是支撑到了七十年代末期;父亲平反后又开始工作,母亲因大病初愈,一直在家中休养。
老屋的记忆,讲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最后再加点料吧。
如今,奶奶、母亲、父亲已相继过世,我自己都成了一个快要退休了的半老头了。
也就在前几年,阿刚伯的儿子有富碰到我,对我说:“什么时候回乡下看看啊?现在搞新农村建设,你家原来的那一片地,都成美丽乡村景区了啊;你要是能来,我有一样礼物送你。”
跟着有富,乘车去家乡看看,果然有种日新月异的感觉,原来的一些老房子,都作了翻新,白墙黑瓦,柳树成荫,几乎家家户户都办起了农家乐。
我家原来老屋的地方,如今改建成了一个小型乡村公园;我突然发现,公园的正中,不正是当年我家老屋门前那棵老榆树吗,依然那么的枝繁叶茂,那口老井,也依然紧紧地依偎在它的身旁。
榆树和老井四周围着围栏,显然是被当作文物保护起来了;这榆树该有两百多年历史了,要是真是我的祖先亲手种下的,想来那老屋要是没拆除,现在也应该成为古迹了。
我的眼睛开始有点潮湿,开始有点想作一首诗的冲动,心里默默地念着:
一泻光阴惊鬓白,
乡音渐近怯何堪。
柳枝指点归家路,
老屋犹知驻巷南。
有富对我说:“这片公园,从设计到建造,我都有参与的,还不错吧。”
我还沉浸在我的回忆中,没理睬他。
有富转身从车里取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块青砖:“这是我建公园的时候,在老屋地基上找到的,你拿着,就当是一个念想吧。”
我接过青砖,有点说不出话,一把抱紧有富:“你,真够哥们!”
老屋有亲情的回忆,很美。文章有精美的语句,很赞。感谢老师赐稿,期待更多佳作。
问候老师下午好,遥祝秋祺,并祝创作愉快。
也许我们是同时代的人,所以对您文章里的描述有一种亲近之感。也是有更多的感悟与感触。
感谢老师对八一社团的支持,谢谢您。
问候老师下午好,遥祝秋祺。并祝创作愉快。
老师的文章耐读,珊瑚昨晚又读了一遍,每遍赏读都有新的感悟,好作品呀,珊瑚学习了。
问候老师下午好,遥祝秋祺,祝天天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