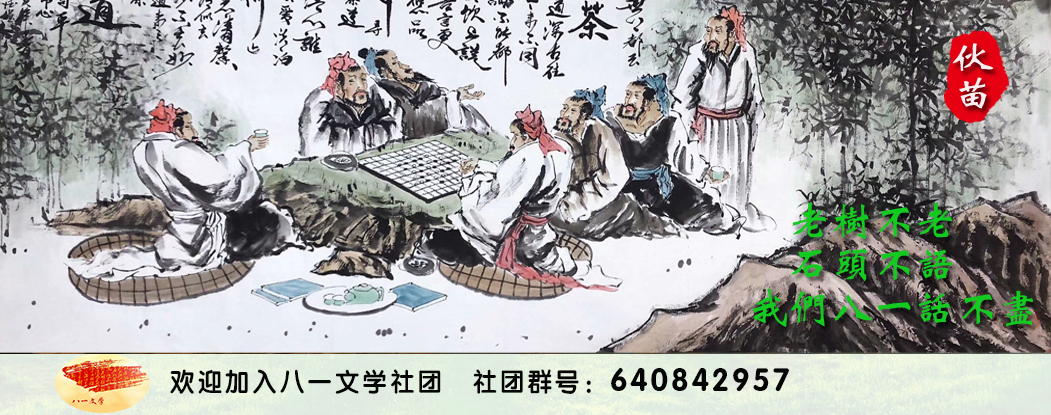【八一】残月(小说·家园)
【八一】残月(小说·家园)
![]()
他明显比黑蛋高了半头,瘦是瘦点,却是精神十足。他小心翼翼地把六中的录取通知书放在窗台上。
窗外,雅马里克山树浓叶茂,欣欣然一片。
五月很久没梦到奶奶和大黄了,他多想趁这个清闲的暑假,回老家一趟看看,快十年了,老家的一切,已是越来越模糊。
这么多年,偶尔父母会带着妹妹回去,而自己总是留在乌市看家。原因很简单,小孩子回不回无所谓,火车票又这么贵。
五月不敢提,只是把这个小小的愿望藏在心底。他知道,高中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自己不能再给大人添加负担。
黑蛋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自从带着刘秘书兼私人助理去了趟阿拉木图,他似乎得到了久违的温情,他唯一的理由就是忙,先是三天两头不着家,后来就是整月的不回家。
凤妮头一回感到了危机,虽说衣食无忧,但她不甘心自己好不容易熬出来的希望就这么拱手让人。
凤妮放下了麻将,想尽了办法,无奈黑蛋就是一条圆滑的泥鳅,怎么也抓不住他哪怕半点把柄。
黑蛋回来,给五月交了学费,饭也没吃,就匆匆走了。
哭、闹,就差上吊了。凤妮不傻,黑蛋和情人早就巴不得自己死了,若自己寻了短,真就便宜了刘秘书那婊子了。
心烦,看哪哪烦。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一个人,伊利老窖、夺命大乌苏,直喝得是天昏地暗,而后鬼哭狼嚎。
“五月,你个小克星,上次咋没烫死你,你死了,这个家就太平了!”凤妮看五月是越来越不顺眼,她认为自己所受的难和所有的不顺,都是因为五月命里带克。
五月不做声,看着发疯的妈妈,等她疯够了、累了,和妹妹一起架着妈妈肥硕的身躯,拖到床上安顿好。
干爹老陈来得勤,三天两头提着酒和菜,两个人杯盏交错,眉目传情。老陈醉不醉不知道,凤妮倒是每每醉得不省人事。
老陈总是有意无意地抖露他那一千多万的拆迁补偿款,偶尔暗示着如果俩人双飞双栖,该是多么的美妙。
老陈甚至拍拍自己干瘪的身躯,无比自豪地吹嘘,依他的体格,随时让凤妮怀个小宝宝不在话下。
凤妮想着要是跟了干爹,自己并不吃亏。她端起酒,“干爹,我知道你行,可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不能便宜了那小娘们。”
凤妮想得不错,只要黑蛋提出离婚,自己怎么的也能分个百儿八十万。
黑蛋更鬼,凤妮和干爹之间的事,他也有所耳闻。他这么耗着,拖着,你个老娘们,你等不得了,自然会离开,至于家产,哼哼。
两个人,各自心怀鬼胎,谁也不想率先捅破这层窗纸。一段时间以来,竟也相安无事。
凤妮是忙着抓奸还是约会干爹,天知道。半夜,她幽灵一般,趔趔趄趄,浑身酒气,有时骂骂咧咧,有时会吐了一地。
五月坐在沙发上打盹,妹妹早已睡熟。
五月把妈妈安顿好,看着她睡下,自己才轻手轻脚地关灯离开。
冬带着阴沉沉的雪扑面而来。爬山虎暗红的根须,裸露在呼啸的北风中,试图抓紧飘摇不定的枝杈。
凤妮觉得再拖下去也没意思,毕竟干爹才是条大鱼,她决定离开黑蛋,带着亲骨肉二丫离开这个可恶的家,离开让她心烦的一切。
凤妮憧憬着未来,她一路喜悦,好不容易在铁西村一个昏暗的酒吧找到老陈,她要和未来的老公最后敲定精彩的去路。
“你真是天真,酒桌上的话你也当真,醒醒吧,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你胖成这样,我和你跑,还生孩子,哈哈,不怕把人笑死!”老陈搂着新认的干闺女,一脸的不屑。
“你,你真不是个东西,畜生,畜生……都……不”凤妮话没说完,“噗通”一声,倒了下去。
等她醒来,已是在中医院的病床上。
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暖地照着病床,房间里充满来苏水的味道。
“妈,您醒了。”五月把头靠近凤妮,“我给爸打电话了,他出差了。”
凤妮睁着空洞的双眼,像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她试图转动她僵硬的脖颈,努力了几次还是没能成功。
“妈,您多休息,爸说忙完就会回来。医生说了,您很快就能好起来。我请了假,您就安心养病。”五月知道凤妮在想什么,他不敢告诉她,黑蛋在电话里说的,咋没摔死这个贱娘们。
“妈,这是我早晨熬的稀饭,等凉凉我喂您。”五月把床头往高处摇了摇。
凤妮感到胸口一股暖暖的东西流动着,她翕动着嘴唇,看看五月瘦高的身影,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
十四
五月尽心地伺候凤妮,有空了看书,困了就趴在凤妮腿边眯一会。
医生、病友,无不称赞凤妮有个懂事的儿子。
“阿姨,看看,我和我妈长得多像啊。”五月头挨着凤妮,搂着她的脖子,冲着护士小姐姐扮个鬼脸,一脸的灿烂。
凤妮“啊啊啊”地回应,五味杂陈。
一个礼拜后,凤妮出院了。住院费加上轮椅,老陈交的费用所剩无几。
“妈,医生说了,只要坚持锻炼,您很快就能康复的。”五月满头大汗,刚刚,他请来社区的几个叔叔把凤妮抬到了家中。
“可怜的孩子。”大家一边下楼,一边叹息。
黑蛋回家了,他乜了凤妮一眼,啥都没说。在他心里,凤妮这是报应。
黑蛋久久地端详着儿子削瘦的面庞,他忽然间觉得欠儿子太多了,都是因为这个死胖子。
他明白,苦难中的十年,儿子像一棵胡杨幼苗,经受着风吹日晒,霜冻雪染,非但没有倒下,反而更加茁壮。
虽然很少参加家长会,可那仅有的两次,黑蛋收获了老师和家长们太多的赞许和羡慕。
黑蛋狠狠地抽着烟,唏嘘良久,而后长长地舒了口气,仿佛这十多年的压抑,在这瞬间才得以排空。
临走,黑蛋又瞥了一眼凤妮,他给五月留了一张卡,“我忙,你把她和妹妹照顾好,钱省着花,用完了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转。”
“爸,我理解您忙,可这是您的家呀,您有空就回来看看妈,她现在这个样子,也够可怜的。”五月低声哀求,他搞不清大人之间的恩怨,他明白,爸在妈在家就在。
“你不懂,大人的事你不懂。”黑蛋摔门而去,一股凉风从楼道里挤进门里,五月冷不防打了个寒噤。
午后的阳光白晃晃的照在窗台上,绿萝因为好几天没浇水,叶片耷拉着。
房间里暖暖的,五月把洗好的袜子搭在暖气片上。他看妈妈睡了,自己便趴在床边,赶紧打个盹,一会要做晚饭,还有明天该上学了。
凤妮的手在五月的短发上轻轻地摩挲着,她没有睡,她听到了五月和黑蛋的对话。
住院的这几天,她把十年的事想了一遍又一遍,五月从那个瘦小的野猫一样的孩子,长成现在精干的小伙子,自己委实没有给过他温暖,哪怕是一丝丝。
她恨自己,不该把怨气发泄在一个可怜的孩子身上。哪怕是开水泼向孩子的那刻,他依然叫着妈,换谁,都做不到。
凤妮感谢死去的姐姐,给她留了这么懂事的儿子,如若好了,我一定待五月如亲生,噢,不,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孩儿,亲生的孩儿。你,能原谅妈妈吗?
凤妮哽咽着,她一遍遍地忏悔,一定要和丑陋的过去彻底告别,她要让五月重新靠近自己。
五月一个激灵醒来,他分明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那是来自妈妈柔柔的手温。
他多想就这么舒舒服服睡上一觉,可是他不能,还有好多事等着他。
天刚蒙蒙亮,雪花纷纷扬扬,昏暗的路灯下,五月瘦长的身影蹒跚着。
公园北街早市,喧闹打破了沉睡了一夜的城市。
在老头老太太们中间迂回,学着讨价还价,五月提着牛奶、鸡蛋、肉和蔬菜,匆匆往回赶。
五月给凤妮洗好脸,一勺一勺的喂她稀饭,“不急,妈,您慢慢吃,我跟老师请过假了,上午早读课可以不参加。中午我回来热饭,您就好好休息。”
看着妹妹走出家门,五月像个大人样叮嘱,“路滑,你看着点车,好好听讲哦。”
五月像个陀螺,从早到晚一直转。他不敢懈怠,不能偷懒,虽然总是觉得累、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妈妈能早点好起来,爸爸能天天回家,到时自己就能痛痛快快地睡一觉,直睡他个天昏地暗。
凤妮因为心情好,精神是一天天好起来。
吃完简单的晚饭,五月先给凤妮按摩了一番,然后推着她在不大的房子里转上几圈。
五月给她讲校园里的事,路上的事,说到有趣之处,娘俩便会开怀大笑。每每此时,二丫总会撅着小嘴巴,装出一副吃醋的样子。
十五
凤妮一天天好起来,终于能借助外力笨拙地挪动身子。
五月把轮椅推到阳台边,烂漫的阳光照进来,暖暖地照在凤妮的身上,缓缓地渗进了凤妮的心里......
“月啊,妈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那苦命的亲妈呀!”
“妈,不说了,打小我就没见过什么亲妈,您是我妈,我答应过奶奶,好好听您的话。”
崖沟,淹没在大山里的村庄,坡上的房子,院子里的大槐树,五月小小的身子后头总是跟着摇头摆尾的大黄。
五月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
亲娘是梅姑,被山洪冲跑了,凤妮是后妈。很小的时候,五月就从邻居小孩的口中知道这个秘密,他并不相信,因为在梦里从来没有见过亲妈,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背影也没有。
有时又有点疑惑。奶奶清明时带着他给爷爷上坟,总是让他跪着给另一个离得不远的坟烧纸磕头,奶奶念叨的什么,他听不清。现在想想,那一定是梅姑妈妈的坟堆。
五月放下书,木然地看了看窗外,初春的阳光照着树顶,积雪正一块块地往下掉。
“妈,今儿难得您精神这么好。我再给爸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晚上我给你们包饺子吃。”黑蛋的电话还是暂时无法接通。
“月啊,星期天好不容易能歇歇,你就别费心了啊,你看你都憔悴了。”凤妮摩挲着着五月粗糙的手,眼里满满的都是怜爱。
五月心里隐隐不安,爸爸的电话好几天都打不通了,该不会有什么事吧。“妈,您先歇着,我下去买点韭菜。”
五月没有见到黑蛋,公司的门紧闭着。透过窗玻璃,依稀可见办公桌上一层浅浅的灰。
在宁夏一个离县城三十多里的废弃的护林房里,放羊的小孩发现了奄奄一息的黑蛋。
刘秘书小鸟依人,风情万种,压抑得太久的黑蛋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
时间久了,黑蛋对刘秘书的新鲜感逐渐失去,他越来越看不惯刘秘书的贪婪。
刘秘书压根就没看上过又丑又矮的黑蛋,她喜欢的是他的钱,而且胃口越来越大,有时直接截留客户的货款,她甚至以老板娘自居,在公司颐气指使。
黑蛋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害怕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这点家业迟早会被这个女人掏空。他开始有意疏远她,躲着她,可刘秘书也不是省油的灯,像狗皮膏药一样,牢牢粘在他的地盘。
黑蛋悄悄转移了公司资产,刘秘书心有不甘。
刘秘书见黑蛋铁了心躲着自己,灵机一动,在手机上留言:前世的缘分不够,注定了今生的分手,为了纪念相识的美好,我想重来一次浪漫的旅行,顺道抹去这段遗憾,如何?
好离好散,黑蛋没想太多,欣然应允。
在刘秘书老家县城的小旅馆,黑蛋正想和刘秘书来个最后的亲热,门突然被撞开了,几个彪形大汉凶神恶煞般闯了进来。
“你个臭不要脸的,老子找了你这么多年,总算抓到你了。”刘秘书被她的“男人”揪着头发,狠劲地扇了几个耳光。
其他的几个按着黑蛋,好一顿拳打脚踢。
黑蛋看看可怜巴巴的刘秘书,自己也确实扛不住了,他妥协了,答应赔偿五十万。他把所有卡上的钱都转了出来,最后又网贷了八万,才凑齐了赎身的费用。
哪知刘秘书一阵狂笑,她圆润的手拍拍黑蛋的死灰般的脸,“老娘跟你这么久,图啥?你帅?坯!想躲着我,门都没有!”
动静闹得太大,惊动了旅馆老板,他看着血淋淋的黑蛋,怕出人命,准备报警。刘秘书指挥着几个男人,慌忙架起黑蛋,扔进车里,狂奔而去。
下半夜,黑蛋被冻醒了,他除了后悔,还是后悔,他怪自己的弱智,不该赴这趟死亡之旅,这个刘秘书心机太深了,她唱的这出够狠、够毒。
黑咕隆通的冷风怪兽般涌进来,包围着他,撕咬着他,他感觉到死神的脚步越来越近。
他看到了爹、娘、玫瑰相互搀扶着,向他走来,又悄无声息的从他身边过去。他伸出手,可怎么也够不着。
远远的,哦,看到了,那是家的窗户,灯光映着五月、二丫,还有凤妮臃肿的身影。
田鼠在黑暗中啃啮,夜枭在黑暗中低吼,黑蛋在黑暗中呻吟。他像一片没有生气的枯叶,躺倒在破败的护林房中。
黑蛋没有死,在县医院被抢救了过来。
黑蛋孤零零地躺在重症监护室,他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凤妮的手机上来了一个河北的电话,电话里的人不屑和她讲话,指明了找五月。
是根生的电话,十年了,五月又听到了熟悉而沧桑的声音。
“五月,我知道你已长大了,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伯伯为你高兴。我在宁夏,你爸也在,他因为一点私人纠纷,被坏人打了,由于他随身携带的东西全不见了,警察根据他住宿登记信息找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