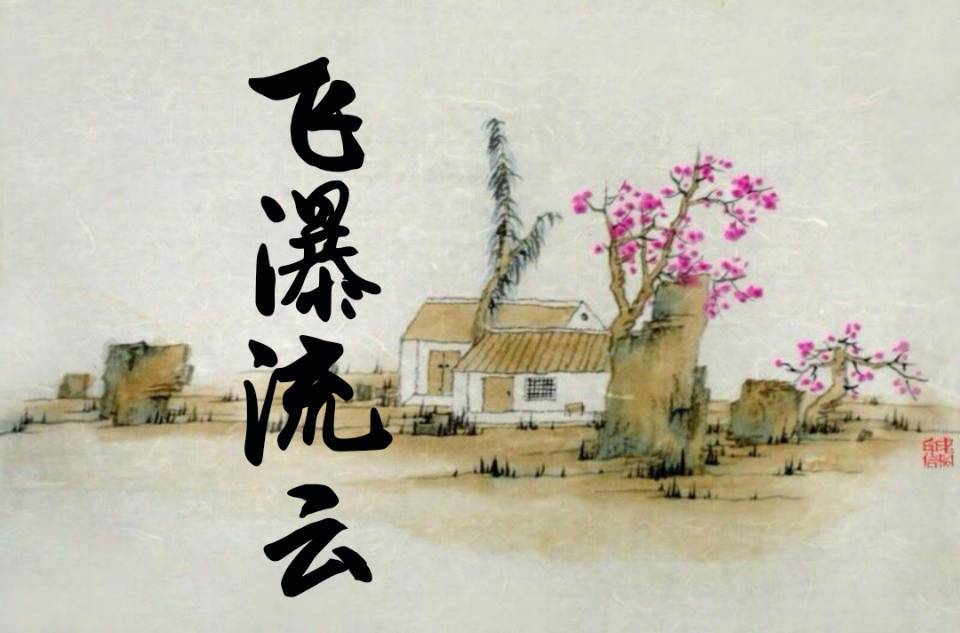【清风】故乡的小桥(散文)
【清风】故乡的小桥(散文)
![]() 王开岭先生在他的《古典之殇》里写过一句话——水是桥的魂曲,桥是水的情书。
王开岭先生在他的《古典之殇》里写过一句话——水是桥的魂曲,桥是水的情书。
我很觉得有些美的意境。
在城市里行走了几十年,见过不少雄伟的大桥:钢筋混凝土筑的筋骨,一律灰白的身子,穿梭不停的汽车在上坡下坡时突突地冒出青黑的烟雾。那些桥连接着城里的街道、市集、花园和生活小区……
桥,在城里是繁华的象征——忙碌而冰冷。
故乡谓之“花园水城”,所以水丰桥密。我独爱那些静静流动的小河,河水清澈,蜿蜒着随山丘的走向而似长龙。也因为河,成就了一座座古朴而温情的小桥。
所以我常常想起故乡的两座小桥。
故乡旧时是古镇,一条小河绕着大半个镇子向西流去。有一座拱桥,横跨在穿过古镇的小河上,连接着镇上的商店与过往的商队。儿时从未见过其它的桥,每每随母亲去古镇赶场,总爱立于拱桥下细细观摩。
一跨大拱,拱的两侧再筑大小不一的小拱,河有多宽,大拱的弧度直径便有多长。桥拱全用红色条石砌成,经年历月,石有斑驳和风化的痕迹;仔细辨别,可见条石上横竖的斧凿纹路来。也有藤蔓蕨草,倒垂而下,更显古朴与典雅。
桥面铺青石,初时凹凸不平,经过世世代代行人踏行,已可光滑照人;桥栏亦用条石筑就,竖石为栏柱,横石为栏杆,用石灰接缝,牢固而稳定。平日里桥上有来来往往的行人——途经的商贾;做生意的小贩;卖农具的乡下人,讨价还价的人们依在桥栏上,三五成群,也不见桥栏松动摇晃。
过桥。紧临桥头有一油饼铺子,热油滚滚,炸得油饼滋滋作响,一清瘦的小伙,围了半截围腰,盯着过往桥上的行人,尖声厉气地大叫:“麻花油糕,一角钱一个!”
于是馋嘴的孩子,便紧紧地依着母亲的裤腿,眼巴巴地望着油饼铺子,“咕咕”地吞着口水。
立于桥上,向西而望,见小河一边排列着泥墙竹篱的民房,民房有镂空的窗子,雕花的窗格;一株硕大的黄葛树,不知生长了多少年,虬枝盘绕,横卧于河面,古意盎然。我那时候常常立在桥上遐想——倘使夏夜,推窗而望,有一弯明月倒映水中,忽听树上寒鸦数声,清风袭来,便可享一夜清凉。
儿时多么地希望在小河边拥有这样的一座民房!
沿河而下,是一排排村庄,青瓦白墙,阡陌交通,偶有鸡犬相闻;有竹林掩映,微风过处,凤尾森森。竹林下一座石板平桥,连接着小河两岸的村落。
桥墩用巨大的红色块石垒砌而成,一块叠在另一块上,就像我曾在藏乡里见过的玛尼堆一样,只是这石堆上并未雕刻着经文与佛语,而是见证了水流冲击的痕迹;岁月流失的沧桑。
桥面不用刻意去铺就,两块修长的石板,平铺在桥墩上。于是暮春傍晚,能看见农人负着犁头,耕牛紧随其后,穿过竹林,走过桥面;夏日里,河水奔流,孩子们在桥下嬉戏——光着屁股,从桥面一跃而起,“扑通”一声,水花溅了洗衣村妇的全身,于是大骂:“你们这些短命娃娃”,孩子不理,半日里从河中间冒出头来,手里举了一条红色鲤鱼,扔向村妇,欢笑声叫骂声伴随着河水的奔流传向远方;倘若秋日,带了弟弟,静静地坐在石桥边,挥着斑竹鱼竿,把希望与等待映入夕阳下的微波中,直到炊烟升起,听母亲立在村口拼命地呼喊,才伴着夕阳西下归家……
幻想的年纪,时常一个人在夏夜里去小河上的石桥边洗澡,那时明月朗照,只听田野里蛙鼓声声,稻香阵阵。坐在桥上,仰望星空,看明月穿过云层,思考着未来的人生,直至夜深人静。
曾几何时,弟兄三人相继踏过石桥,背负行囊离开村庄,不见清晨的光辉,但闻小河流水的“潺潺”之音,还有父母远送的身影。
在乡下,桥是村里往来的情感之路;是通往村外大千世界的希望。桥连接着温情,见证了乡村的变迁。一座桥,便是一个地名,也是生命的一个据点。
人只有跋涉过万水千山,踏过不同的桥,才知道人生是什么模样。所以村里的老人常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行过的路还多!
故乡的小桥,它连接着儿时通向未来的梦想,也连接着他乡人对故乡的惆怅……
2019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