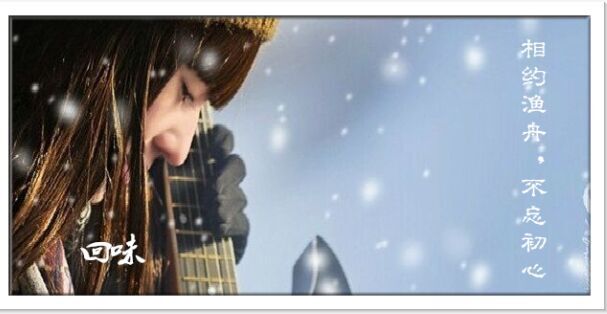【渔舟】庚子春:访小古堂(散文)
【渔舟】庚子春:访小古堂(散文)
一
初识小古堂,是2016年,彼时因在学而优书店就职的缘故,对广州实体书店群乃至整个实体书店业都关注了一二。若说学而优是广州最大的实体书店,那么小古堂只需加个旧字——广州最大的实体旧书店。21世纪初,小古堂以网上书店起业,数年后增设实体书店,自此以实体网络并行运营至今。
从前去小古堂,盖因慕名而往,或因淘书、避难而去——我始终认为:书店,是心灵的避难所。在学而优工作时,饱受书山重压折磨,是不曾有余力去小古堂看看的,然此番再度去访,确因了小古堂网上书店的缘故。
南国的春日里雨水淅沥,于孔夫子旧书网搜寻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类书籍以消磨度日,见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的《古琴曲集》可购,从前在大佛寺古琴班上课时,老师曾发过该曲集里《凤求凰》与《高山》的曲谱,是一本十分重要且难寻的琴谱。见售价合理,再看店名竟是小古堂,忙与店家询问可有实物。因上架日期是前一日,摸不准何时便没了,按捺不住迫切的心情,晚间就连忙赶了过去。
上一次去小古堂之日已恍如隔世,是以不知其扩张装修翻新过,绕过了一大圈路才顺利抵达。直见到《古琴曲集》后才安心打量起这屋子里的万千架上书来,原先颇为拥挤的书架两侧现已十分整齐,想来是因扩张面积有原先的一倍之多,空间绰绰有余。眼前数十米长的临街玻璃墙让视线极为开阔,墙壁上、书架上也悄然添了许多书画作品,浓淡相宜的水墨色,不喧嚣,不夺目,仔细瞧来真是雅致得紧。
随手翻开一本《初刻拍案惊奇》,泛黄的旧书页里墨香氤氲,是久违到近乎忘却了的感动。与之媲美的还有那一本本二十世纪出版的书籍封面,多以淡色图纹做底,右侧书法题名,古朴淡雅,令人一见倾心。素日里于电子屏幕上流连图片已然很触动了,而此番亲眼所睹,亲手所触,总叫人不经意就眼眶湿润。
时间流淌得抓不着痕迹,直到店家提醒我要打烊了,才粗粗浏览完一半原先的区域,而另一侧新扩张处已关灯。只得趁结账之际,借了路灯亮光匆匆打量几眼,靠墙的书架与窗相对而立,一眼便可达尽头。于昏暗室内远观窗外榕树掩映下的车辆与行人悠然来往,我只是遗憾又惋惜地想着:若逢晴朗的午后,无论春夏或秋冬,这里都是绝佳的一隅啊。
只是,我还能来几次呢。
欣然怀抱八本旧书,如获至宝,用店家给的塑料袋裹着,至下楼后,才发现空中飘起了细雨。沿着中大校园的红砖墙,独行于夜色里,我把这个愉快的消息传给远方的长安君。
二
午间常在学而优书店溜达,偶然一日与一平提及小古堂,当下就约定了一起去小古堂。
除丁酉年元夕招待远道而来的柳老师外,是不曾与人一同去过小古堂的。
因着这份约定,我原本跳动不安的心忽然就踏实了下来。
沿着西门,至南门,又至东门,过红绿灯,准确无误,一路十分顺利。
比之独自看书,与友人同行是一种别样的愉悦。各自看书,有合适书籍时,轻声讨论一二,很意外一平懂得我感兴趣的范围,这使我有些动容有有一种知音难觅的隐隐难过。
当年我与一平同期入职学而优书店,后因生计所迫离开了,两年后再度回来,如今又不得不离开。
一平却是一直都在的,曾去过289艺术园的分店,如今又打理网店,还时常支援店务。是以,当看到某些熟悉书,我们也会互相提及它在学而优的故事。
看似平常的书店,承载了店员、书籍、读者间千丝万缕的故事与情谊。
这情谊也不尽然都是美满的,比如《汴梁琐记》与《红楼梦人物论》,我们都想买,但店里各仅一本。起初是一平将《红楼梦人物论》让与了我,说是自己不记得原著了,需先去重读原著。而《汴梁琐记》归了一平,我倒也未翻全内容,只是近来颇为爱好地方志一类的小品文集。若是太过于专业的,反而因学识所限读起来吃力又费时,精神满足则无从谈起了。譬如《扬州地方文献丛刊》共十册,我虽极为喜欢,却也仅《扬州名园记》稍微可读懂而已。另有《扬州画舫录》也是早就心仪的扬州方志了。
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焉知何年何月才得以览尽所欲读之书呢。
好在是趁兴而往,尽兴而归。
小古堂不是广州唯一的旧书店,但是最大的文史哲艺术旧书店。
旧书与二手书是有区别的,旧书也可以说是已绝版的古籍与图书,但二手书更多指向于非首次交易的仍在版书籍。举例三月前出版的书,即使倒卖过数次,也只能算二手书而非旧书。一点个见,望海涵。
正因为小古堂(与学而优)的可贵,我便无法痛快地期待离开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