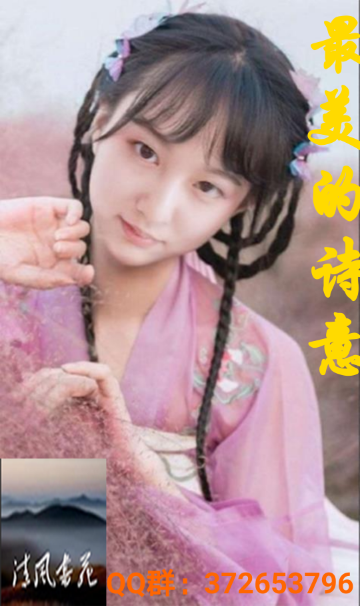【浪花•感动】忽惊老村刺眼来(散文)
【浪花•感动】忽惊老村刺眼来(散文)
![]()
一
因防控疫情,三四个月居家隔离,年轻人的性情被打磨得软润起来。我外孙说,我们学校“陶情养性”的修身目标是在家实现的。说话里,多了抱怨的意思。而我的忘年交老乡慕老也耐不住这份寂寥,他要找一个宣泄口。
正月十五,梦中白浪款款涌岸,漫流过桥,入村没地,唯见屋舍在水中,突然天降轻舟一叶,弄船人吆喝一声“客官登船”,慕老一个健步,孑立舱心,绕弯拐角,巡村逛街,六十年代旧村,一个个屋主隔着窗棂摇手邀家。他叙述这个梦境,恍若穿越,返回少年老村顽皮时,“夜深忽梦少年事”,不胜感慨。一夜恍惚,却有身处“满船清梦压星河”的浪漫佳境。
梦醒之时,慕老叹息一声——忽惊老村刺眼来。屋舍俨然,旧人鲜活。村中一老,忘记姓甚名谁,叮嘱慕老,说,原始村貌,堪比《清明上河图》,可绘制于宣纸,与之呼应,双绝并存。
慕老一辈子与算盘打交道,指长若葱白,抚弄珍珠万千,都在一木框间。他左手摸右手,一指权为狼毫,怎么也提不起,可梦中明明要他做一个老丹青手。时年77岁,60年前,是17岁懵懂少年,喝狗唤鸡,沿街痴狂,不曾想,要绘一幅村居图,实在为难了。且古语说,人到三十不学艺,年过四十不读书,几近耄耋之年,原本也不是年少冲动岁月了,如何大器晚成?珍珠手(打算盘,慕老常称自己是“珍珠手”)变写字画画的“狼毫手”,这可不是职业转换那么轻松。
这个怪异的梦,被他的老伴知道,说,不是有诗说“但愿归来还少年”么,要不要给你做个滑冰车刻个陀螺猴?这份嘲弄,没有打消慕老的返老还童之愿,其心情反而越发急切了。打电话给鸿宇文具的老孙头,破例开了文具店的门。狼毫三支,版纸十张,檀皮徽宣一刀,辉柏嘉彩笔提包,竹旗牌丹青垫……好家伙,这些专业人士都不能俱全的工具摆设和行头,都被慕老搬回家。
置于大衣橱上的外孙上学的文具也重见了天日,圆规三角板,铅笔加直尺……原本老伴以为老慕就是瞎捣鼓,就像小孩子贪玩,即使这些文具用不上,还有一个外孙在上学,也不废弃,谁想到,老慕动了真格的,老伴看他动如顽童,不觉好笑起来。
老伴的裁衣案成画案,结婚时的一对花瓶,一个成笔筒,一个成洗墨池。历时68日,就像武汉封城的时长一样,慕老居家,远达楼前院,近在八平书屋走山水,老家南桥头的风光尽收笔下。
很长时间,自觉遵守居家令,闭门不出,5月16日,慕老终于耐不住了,清晨就电话相约,去茶舍看图。我说看什么图,是看一腔心血在花笺上摊开、流淌……
我是唯一可以与慕老一起怀旧的人。他老伴缝制的金丝绒布料做外套,精致的拉链,闪着古铜色,仿佛是文物出土的感觉。我明白,此时,这幅“村居图”就是他最心爱的宝贝,哪怕呼一口气,都会伤了软纸新彩。
画上老村“刺眼来”,也暖着我的心,唤回了我温暖的记忆。
二
徐徐展开,“忽惊老村刺眼来”,一下子将我的身心再次拉入故乡的怀抱,一抹乡愁竟然可以完全铺陈在画纸上。我笑慕老有“乡愁满目生”(钱起《送征燕》)的怅惘与悲切。长若三米的美图,就是我的故乡,纵意拥抱,再一处一处仔细端详,惹得慕老怪眼看我多时,他比我还得意。
西层峦,北叠嶂,东簇峰,半抱故乡到如今。连绵的山,曾经印着我的足迹,依然有着“踏遍青山人未老”的从军行感觉;山吟风,风作诗,我也生出少年青涩的情怀,想登山展臂吆喝一声:游子五十载,终于回来了!
一条宛若飘带的村河自西南缓缓荡来,穿过“九大桥”掉头而东。那个老鳖湾,我和小伙伴曾经于中午藏在草丛里偷窥鳖爬巨石晒鳖盖;扬水站下是蓝蓝洞,河水碧蓝,不知其深,曾经一跃而入水,只是那次足足五分钟没有爬到水面,是五年级的“老大”连聚哥一个猛子下去,老鹰抓小鸡般将我提了上来。九大桥下游是我家岸边小菜园,1967年那场洪水,摧枯拉朽,半边菜园卷入洪流中,雨灾之后,队长步量损失,在北山后再辟半月地,算作补偿。陆游曾经“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我将故事藏河中,河水泛波,掀起了我记忆的碎浪,绵软如水,情长似河。
老街最善藏故事,门前老街拐过三道弯,那是我们捉迷藏的地方,老槐树在老街头上,还在那里做路标。村中路,当年村上买来拖拉机,书记在桥头把旗一挥,轰鸣响全村,红色的拖拉机头喷着浓烟,仿佛万马奔腾,绝尘远方。沿河路,名字老土,可河边响起的棒槌捣衣声,将这条路也弄响了。记得,当年走这条路,脚下都是节奏。那些年,尽管日子艰难,穿衣不暖,可南河东河晨兴的雾带,就像是一道绕村的暖气管道。我想起了妈妈,将这个想法告诉你,你吃醋地说,比妈还暖?我笑着狠劲地摇头。
刺眼扎眼的是我家老屋,一眼就盯住了这座北山根下的茅舍,画中的墙壁上刻着我父亲的大号。难得慕老为我惠存六十年代初的记忆。逼仄的长院外是四季小土肥场,沿着场地半边是“禾场”,隔近邻居的麦秸垛玉米秸秆垛就像是蒙古包一样,密布四周,记录着那时候的田园日子,日子里藏着我多少快乐,晚放学后,我们将书包撩在我家街门前的长石条凳儿上,分组捉迷藏,从草垛里把谁揪出都是一阵惊天的喧哗。慕老再现了纸上的童年记忆,唤回我的青春本色。画是否美观逼真,颜色鲜艳与否,不管不在乎,记忆亦如当初,别的都在其次了。李白曾经写自己的恍惚感觉“杳然如在丹青里”,我也有这番唯美的体验。
老街向西,到我家老屋西就戛然而止,被老国治哥的老屋山头挡住了去路。突兀而起的房山头上写着“吉星高照”四个黑色的“抬头见”的字,令我想起父亲和我说的1956年购置这座老屋的故事。
“吉星高照”是住宅的最高标准,而被国治哥老屋逼到一角的三间房,从风水上说已经无看点可言了,当初风水先生摇摇头,好像找不到一点可取之处,只有父亲一再坚持。他给我爷爷买下一处五间房子,我的目光循着画上屋舍,移至老村中央位置,也有名字赫然入眼,爷爷的房子还在画上。父亲囊中已经羞涩了,价格优势,使他下定决心,一把掏出了上千元,买下老屋。给老子置屋于村中央,且五间大舍;自己蜗居于村之一隅,是三间草屋。一个“孝子”的名字属于我父亲了,父亲也为此自豪了一辈子。他说,既然抬头就见“吉星高照”,那就属于老街,我们跟着沾光,风水自然就好,有什么不可。这是无奈的说法,但显示了他追求安居的心愿。我清楚地记得,“除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奏响时,“吉星高照”四个字就被白石灰抹掉了痕迹,父亲说,你国治哥流着泪看着四个字消失,父亲用拄着的拐杖在石头上敲着响儿抗议,无效。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影,一根拐棍怎么可以挡住呢。时光啊,很体贴人的记忆,这幅“村居图”将这一幕重新唤醒了。很多东西,抹不掉的,就像父亲说的,你剪掉一张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往往会在头脑里刻下那篇文章的所有字。这是我上学时从父亲买回的旧报纸剪掉小豆腐块文章时的对话,当初一点不懂,现在我明白了,记忆是“剪不断”的。四个字消失了,可在慕老的笔下出现了,慕老说,这是不能消失的记忆,就像“永不消逝的电波”。
三
留住曾经的影像,喜欢画上唯美朴素的光景。这是慕老告诉我创作这幅画的初衷。没有高楼,只有茅舍,海草房泛着被白色时光洗礼的颜色,百年不坏,画面上连屋脊上长着的野草也生发了灵性,似乎与赏画的人挥手致意,满目亲切,草木的世界,总是会生出烟火,眼前浮现出炊烟袅袅的样子,甚至我嗅到了晚饭的香,只是听不到妈妈一声“X儿吃饭啰”的吆喝声。慕老说,他创作这幅画的时候,是想与那些老去的人见一面,一一对话。
土改后建设的新房,屋后都插上了拴牛桩拴马桩,这是合作化时期的标志。南河是一条龙,不知这个论断谁做出,自然灾害过后的十年间,青年建房娶亲的新房一溜排开,创造了“小桥流水人家”的静谧画面,尽管历经半个世纪,房屋都染了旧色,但依然保留着从古而来的古韵史香。
关于村子的记忆,那要找村子里的“知事”来唤醒填充,他们是村子自然留下的活字典。金元时期,设“知事”一官职,其职级相当于后世的“知县”,这样的人是在元帅府、大宗正府、司农司、大兴府等官署做首领官,类似于秘书长一类。慕老请村中三五个德高望重且在记忆上不逊色于年轻人的长者,呼他们为“知事”,相忆村中走出的人,至今已有三四辈繁衍,用大数据推算,在外的人也有两三万了。每年清明节,很多并不熟知的脸儿就在村中和四野露面,除了祭祖,看望老宅,临屋生怀念,可有些屋舍早已是残瓦断垣,不堪目睹了。
慕老一一将屋舍归位,一户不失,告诉我,村子共有829户人家。我逐一寻名,想唤出我有限的记忆,可连名字都陌生了,哪有什么故事了。98%的户主已经魂归四山了,我不胜哀婉。就像我记事看见的“神主碑”,写着“XXX之神主位”,给我的是物是人非的伤感。慕老说,创作这幅画,一直跟那些老者对话,房舍记住的是人丁的过去,他说自己的记忆总是在色彩里,他用了一句“朱颜不老”的话,来形容脑海里的村落房舍模样。他说代销点那是地主的房子,朱门依然,后辈黑漆图新,是农人的手的颜色,最耐看。我道“问舍主人皆不语”,慕老说,留下“画语”给后人。是啊,老心多感慨,总是为后人去想,人固有一死,因而人们总是热爱后代,慕老有三个女儿,早已出嫁他村,按照男嗣的观念,慕老是无后的一类,他说,最终老骨也要归村,女儿的根还在南桥头村。
丹青不知老,依然朱彩艳。也许,一个老人想找到一处早年的春光葳蕤之地,才诞生了这幅画作。其实,我的理解有些肤浅了,慕老一直在笑。他还是忍不住告诉我,他要将这幅画做精致装裱,赠与村委会办公室,为子嗣们再来寻祖居提供一幅攻略地图。是啊,连我老屋所在的老街也没有剩几户人家了,村西绕水而建的高楼拔地而起,80%的住户已经陆续迁居新宅了。百年之后,谁还会找到旧村的影子啊,留住一段影像,为这些高楼做底色,不忘我们曾经蜗居于此,感恩当下入住新楼。慕老没有说这个意思,可我一下子就读出来了。
不胜感慨啊,我能够为养我之南桥村做些什么?慕老原来也知道我这个从这个乡村走出的人乡愁难释,嘱我为之作序——
《南桥村居图》序
不再感慨沧桑埋红尘,不必轻言村居之微俗。看见老乡宗范先生所绘南桥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村居概貌,心生感佩,勾起我之暖忆。“云破林梢添远岫,月临屋角分层阁”。一幅美图出境界,一抹乡愁添温情。不是历史让人记住什么,而是留住丰满的历史情怀让人堪回首。宗范先生从未沾丹青,却可筑涛笺上屋舍千间,于是,南桥多了一份厚重的承载。村居图之屋舍有主,细读,可唤起那时节相处之和睦生动的故事,给后人留一份可随时打开的影像,笔走飞檐,墨绘流水,其才胜弄彩人,其情直攀上河图。张择端之《清明上河图》,泻汴梁繁华街市之风情美韵;宗范先生之《南桥村居图》,现一方宝地嘉池之风水人脉。媲美犹可也。
宗范先生嘱我为小序几字,收笔不住。村居图之精彩,岂是文字可通透的,愿与有意此图者索看,以慰乡愁,觅到祖居之地,惠存一世深情。
时在庚子孟夏五月
怀才抱器行文
老村的屋舍是我们珍藏生活的外壳,也是留住烟火的象征。于我,是牵动乡愁的木刻版画,凸凹有致,棱角分明。旧的村落,无法重建重现,但可以刻成最美的画,我为慕老的创举感动了,眼睛盯住每一处屋舍,还原儿时模糊的印象,努力留住那时光。
乡愁,是不管过去多少年,在游子的心中总是一幅画,无论怎么褪色,在游子心中都是光彩耀目;是步入年老也还冲动地把记忆变成少年时的风景,多少年都是动感十分,栩栩生动。一抹乡愁,有多浓厚,可以使一个一生疏于丹青的人,一夜之间突然变成最美的丹青手啊。
“刺眼”的不是堂皇的琉璃瓦舍,而是几间败草覆盖的老屋。所谓梦牵魂绕,不会因村舍的低矮而梦飞走,我的梦,我的乡愁,也在慕老的村居图里,精致,可感,可藏住我最本色的怀念。
有些日子没有提狼毫了,眼也低了,手也拙了。宗范老乡非要我写序留墨,我拗不过他,说字丑不能见人,他一句话让我找不到任何借口了:村居图也有你的时光,你不走进谁走进!
2020年6月8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