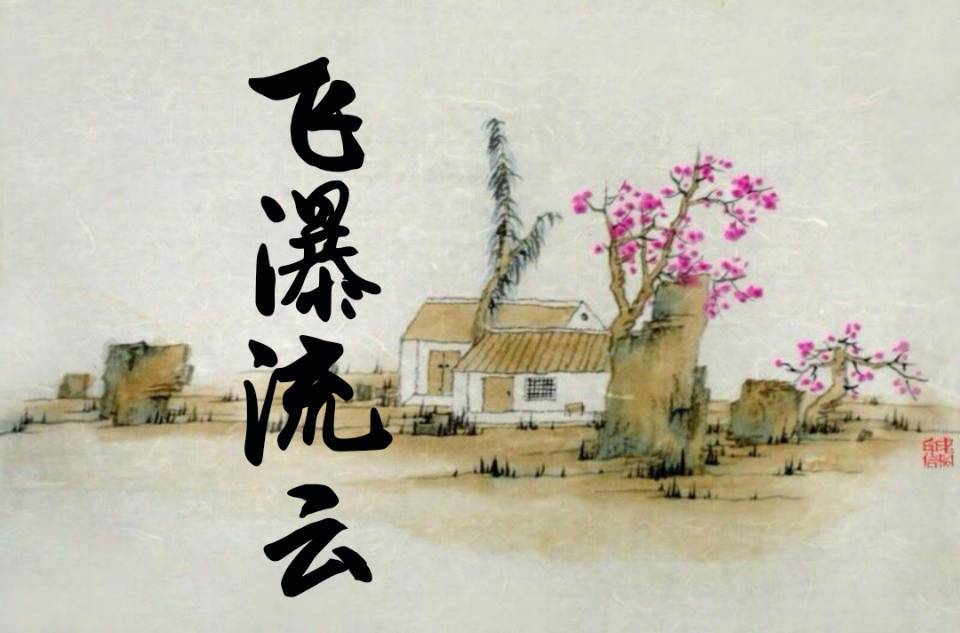【清风】儒说(散文)
【清风】儒说(散文)
引子
在济南百花公园西门的左手,闵子骞纪念馆既醒目又寥落:大概是因为需要五块钱的门票,所以那天下午,整个纪念馆只有我一个人;半个月之后再次凭吊先贤,情形还是一样。
在大明湖南岸,供奉孔子的文庙,占据着黄金位置的核心,甚至是整个济南黄金位置的核心,面积有一万多平米,建筑群雍容肃穆。里面游客稍微多一些,但与墙外熙来攘往的场景远不成比例。还是因为几块钱的门票,一下子挡住了太多的人。
也许,这就是今天儒家学派的写照:近几年,因为国学回归,于是儒家大院的门楼、牌坊气势宏伟,看上去光彩照人。可是,要想登堂入室就得购买门票——需要去认真研读,仔细思考,甚至皓首穷经。于是,里面经常门可罗雀,而且,即便是这样,仍然有很多人不过是景点打卡而已。
到了中高考,或者其它“做交易”的时节,文庙的人会多一些;不过,闵子骞纪念馆不行,因为它不是可以做交易的地方,去那里的人,需要发自内心的挚爱。
可是有几个人是发自内心去挚爱?而且,就算下决心去挚爱,又准备爱它什么?年代太久,蒙在儒家先贤身上的尘土太厚,稍微靠近,扬起的灰尘就要呛人窒息了。
然而,儒本来不是这个样子;将来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当然,也不会是最初的样子,因为经历二千多年风雨之后,这个世界变化太多,它也不应该,也不可能停留在原地。
那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又该在哪里安放?神坛、祭坛、书本、墙上,还是把它运用到日常工作中来,成为服务于国家、社会、民众的有力臂助?
笔者认为,今天的儒,应该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以宗教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应该走出“自闭的、孤芳自赏的小圈子”,风风光光走到广大民众中间,发挥它的作用。
1.宗教的意义
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下子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节奏,我被隔离在遥远异乡的某个酒店,然后就有了娱乐时间,一下子看了好多部电影:从亚历山大到古罗马,从上古神话到现代无厘头。说实话,让人怦然心动的情节不多,因为我发现,在电影里面,只要有人的地方,或者被庸俗、无聊所缠绕,或者受困于阴谋诡计和卑鄙无耻,或者被奇怪的狂想、妄想所左右。而且,人们总是在急急忙忙打破眼前的一切,将井然有序变为混乱不堪。
其实不止是电影,看看我们周围,情况也差不多。太过自我的人类,看上去那么小器、自私、贪婪、阴险,似乎下一秒就会坠入深渊。
然而当我们回头望去,就算是再盲目、再偏执的人都得承认,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往前发展的,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手铐脚镣的奴隶社会一路走来,处处都是发展的痕迹:古罗马的斗兽场成了遗迹;徭役赋役的血泪走进历史深处;人类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彬彬有礼、讲究公德;更不用说工业现代化的伟力——便捷的交通,星罗棋布的摩天大厦,以及更民主、更公平的社会生活方式等等。
难道没有人察觉这里面藏着极大的悖论吗?个体想去阻挠,想去破坏;而由个体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却在大踏步向前发展,其中的缘由是什么?
如果你深入去想一想,也许并不奇怪,因为人类社会的集体意志,不是个体意志的单纯集合,而是由人类的集体理想赋予的。这种集体理想,更多考虑的是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同时把集体对未来的展望和愿景添加进来。只要集体意志在起主导作用,那么,即使存在个人的“拆台”行为,也不能阻挡集体向前发展。而当这个集体崩盘,它会加倍需要集体意志来重新聚拢——或者伤口愈合,抵抗能力变得更强;或者被其他集体吞并,被更强大的集体意志所替代(在这期间,该集体的地位往往堪忧)。
当然,集体意志不一定都是向善的,当德意志第三帝国被希特勒左右,就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英法之间相看两厌,就有了百年战争。然而,从长远来看,必然是邪不胜正,因为今天人类取得的辉煌成就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通常来说,越是经过重大挫折,向美好愿望靠近的步伐就走得越快。
这样看来,人类社会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个体,一部分是集体;而集体在运转过程中,同样有两套规则在并行:一套是规范人们行动的刚性管理制度;一套是这个集体的集体理想。这两部分本来不分伯仲,只不过第二部分不容易被量化,所以经常受到轻视。
即便受到轻视,它也从不缺席。
在过去,同样是奴隶制国家,古罗马和商周帝国,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同样是酋长制国家,在阿拉伯半岛和在中南半岛就迥然不同。这些差异,就是由于集体理想不同而造成的。
不止是这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南韩的政权就进入动荡模式,总统不停被弹劾,各种政治丑闻层出不穷;泰国也是这样,而且这个“微笑的佛国”,动不动就真刀真枪地在曼谷大街上干起来。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这一期间,两个国家的经济都在快速发展,各项公民指标也在提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刚性的社会管理制度在运转过程中受到影响的时候,柔性的集体理想开始接管它的部分职能,而且比起应该起到的作用,它做得更出色。
集体理想不但对集体影响重大,对其中的个体,影响同样巨大。正因为有美好的共同愿望,激励人们不停向它靠拢,才会产生那么多可歌可泣的勇士;才会诞生那么多公而忘私、舍生取义的英雄;才会有那么多寻常人甘于为集体奉献。
集体理想不是吟诗作对、道德文章,虽然它也包括这些内容。它的初等表现形式就是集体内人际关系氛围:项羽比刘邦更像个贵族,更像个杰出领袖。然而韩信、陈平、英布、彭越,还是纷纷跑到了刘邦那里,就因为刘邦那里集体氛围要强过项羽。
人际关系氛围再升版就是文化。今天的美国,最强大的武器也许不是航母、核武器,因为这些东西威胁不了野老村夫,威胁不了市井小民,威胁不了沙漠与深山。但是电影、音乐、NBA,却让无数人对美国心向往之;自觉不自觉套用美国标准来评判周围的人和事物,将社会环境与美国对标。而且,越是那些没有去过美国,对美国一无所知的人就越是迷恋,将美国一再神话,远超过它本身应该得到的赞誉。
文化再升版,就成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也就是宗教。而升版成宗教之后,它就能超越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超越族群而存在——欧洲经历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经历无数次战争,无数个国家兴起灭亡,但是基督教始终在那里;儒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也是一样。
在国内,很多人不喜欢宗教这个字眼,提到宗教,觉得那就是封建迷信、封建糟粕,或者与奥姆真理教等类似邪教组织联系在一起。说起宗教,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就是,有人占据高位之后,行招摇撞骗之事;有人一直跪拜在那里,愚不可及地磕头跪拜。
那么,什么是宗教?
对于宗教,不同人有不同定义,不同人有不同认知。而且,即便是同一种宗教,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中间,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要搬书本逐一去考证,可能需要长篇累牍。而笔者认为,在今天,只要承载人们美好希望,给人们以心灵寄托,有理想、有纲领、有组织、有传承的思想体系就是宗教。
一句话,宗教是人们灵魂的栖息地。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学就是宗教,因为《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儒家的大同世界,不论男女老少都容纳了进来,让他们有栖身之处,自然就是宗教。
当然,属于意识形态的宗教,需要借助一定载体呈现出来。在呈现过程中,一些人把自己的私利添加进去,然后宗教就部分成了牟利的工具,进而与愚昧、顽固、僵化、阻碍社会发展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包括世界上其它宗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存在这个问题。甚至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不过,即便带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宗教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就像人的肉体需要容身之处一样,人的心灵也需要归属之地。
欧洲在中世纪走向终结之时,人们为摆脱了基督教的桎梏而欢呼雀跃。然而这场全民狂欢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偃旗息鼓了——宗教的枷锁让人透不过气来,但是失去约束后的人们变得更加可怕。思想的迷失,带来的是行为的肆无忌惮;缺少道德约束的白人,犯下了比前人多出千百倍的罪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何止亿计!然后直到自己也不能忍受,不得不选择重新回归宗教。当然,回归后的基督教,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已经有了天差地别:宗教基本上与政权脱离,不再有专制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们可以对它说“不”,所以宗教变得慈爱、纯净、亲切起来。
其实我们也经历了这样一段时期,直到现在,也在承受它的疼痛——几十年前,宗教被剔除出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又没有找到足够的替代物。于是,中国人,曾经被全世界公认为最“彬彬有礼”的人,变成在很多国家和地方讨嫌的人。更严重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明明已经小心翼翼,却还要遭受“另眼相看”,这种情形直到最近几年才慢慢好转。这是我们自己的切肤之痛,也又一次证明人类所具有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宗教。有些人天生就比别人坚强,神经比别人粗大,然而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毕竟,连国父孙中山都信奉基督教……
不要因为少数人物的特异,就抹杀大多数人的需求,同样是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教训。
宗教为什么会有这种作用?那是因为,除了一定的督导功能,宗教还有审判功能,基督教的“炼狱”,印度教、佛教的“轮回报应”,儒教的“荫及子孙”,都是审判功能的体现。由此带来的思想内视,由此形成的社会舆论氛围,都在有形或者无形纠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2儒教的作用
在国内,我们很少把儒家当成宗教,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学问,或者一种人生态度来看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儒教与其它宗教有很大不同:儒教的核心是四书五经,对这些书的理解,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方面,儒家与印度教有相同之处,印度教的核心是《吠陀经》,同样允许人们自由发挥。
以书为核心的好处是,一般不会形成宗教信仰约束和信仰枷锁,所以中印两国的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都享受了充分的信教自由。这与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的教众,饱受宗教剥削和宗教思想拘禁形成对比。
但是儒教与印度教相比,还有很大区别:印度教在印度建立起了庞大而又有实权的婆罗门阶层,这个阶层的首要任务就是不停宣讲、灌输婆罗门教义,并且以此牟利,同时压制其它阶层。而儒教没有形成这股力量,它对人们的作用主要是劝诫,并没有多少强力手段。在这方面来说,儒教大概是世界上最宽松、最宽容的宗教。
应该说,儒教从西汉时期正式进入国家管理序列之后,它的地位就一直比较尴尬,因为儒教并不是封建政权唯一选择,统治者更经常的做法是“外儒内法”。于是,经常会出现需要的时候捧起来,不需要的时候搁置一旁的情况。这也造成儒教看上去既任性又脆弱,既高光又无力的局面。
儒教作为宗教,除了像其他宗教一样,给中国人一个道德和心灵的归宿之外,它还给了中国人一个中华民族的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大家统一在华夏文明的旗帜之下,进而认同这个国家,形成大一统的格局。并且,无论是谁当政,只要不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会受到谴责,遭到反对。而历史一再证明,统一的中国充满活力;分裂的中国动荡不安。
今天,要界定一个人中国人的身份,有很简单的办法:身份证、户口本、暂住证等等;在过去,界定一个人的身份,是把几家几户连在一起的保甲制度,防止人口流动的重农抑商制度,还有作为身份证明的“过所”等辅助手段。那么在过去的动荡时期呢?当这些制度都失效的时候,又该如何界定一个人的身份?辛弃疾明明生在金国,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回归自己南宋臣民的身份?白朴明明是元人,为什么宁愿做浪迹落拓的汉民?
打开世界地图,你会看到从古到今,许多国家走着走着就走散了,走着走着就走丢了。埃及、巴比伦、伊朗、土耳其,因为遭受外族的入侵,割断了与古老传统的联系;而几度统一的中亚,因为找不到继续在一起的理由,现在四分五裂;西罗马延续了上千年,一朝被打散,就再也不能合拢;面积与中国基本相等的欧洲,目前被拆分得稀碎;日不落帝国,重新蜷缩回自己的小岛;还有美国和俄罗斯,看起来都很强大,但如果受到强力冲击,国民和疆域还能继续粘合在一起吗?俄罗斯已经分裂过一次,那么美国呢?
正视国学、正视传统,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许多同胞都看不起国学,之所以看不起,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或者误解太深。看网络上的喷子,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喷什么,偏偏喷得十分起劲,这真是一种悲哀。
人都是由肉体和精神两部分组成的,当生命没有保障的时候,肉体重要,当人们吃饱之后,就是精神重要。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体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刚刚摆脱温饱,还没有完全习惯更高层次生活的转变。然而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责任之一不就是预见明天,预见未来,给社会发展一个方向吗?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