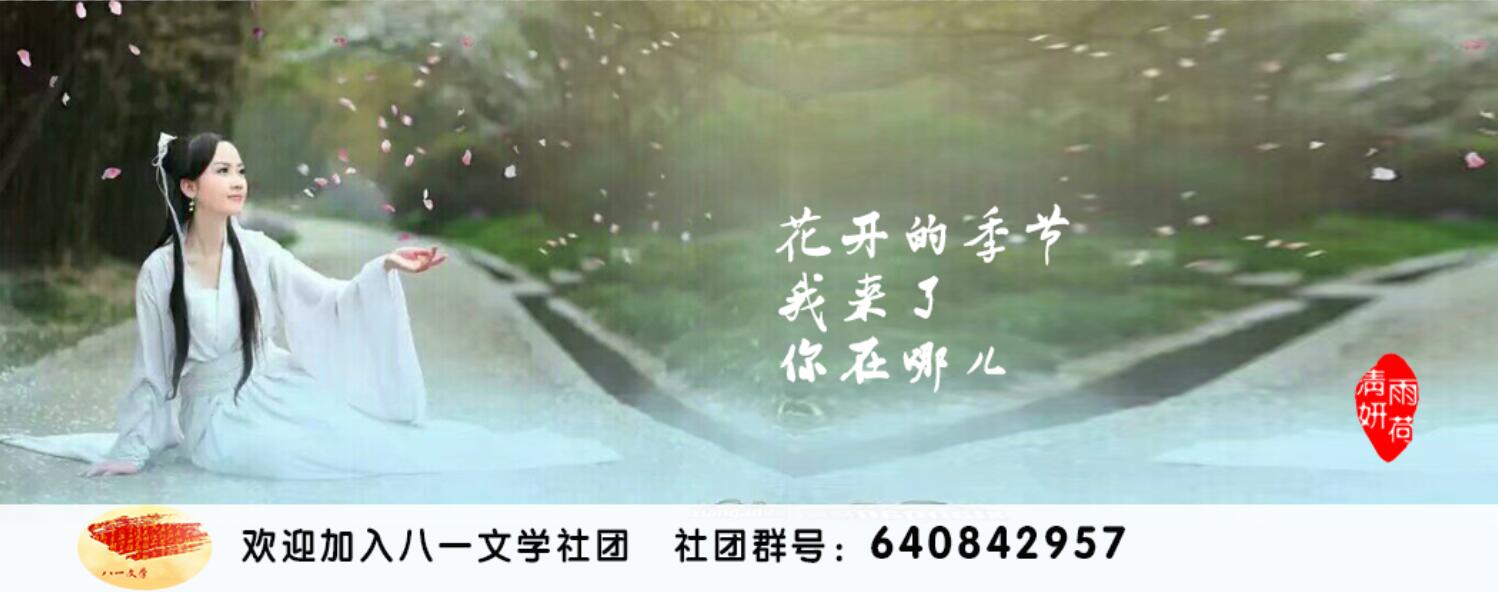【八一】姑姑(散文)
【八一】姑姑(散文)
![]() 一
一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姑姑开了一家饭店。饭店兼住宿,姑姑是饭店的老板娘。姑姑四十岁左右,长得很漂亮,又黑又大的眼睛如清水般明亮。她常梳着两条小辫,像两只漂亮的蝴蝶在店里飞来飞去。姑姑精明干练,做事利落。她与人为善,团结相邻,方圆几十里的人不管是认识她的,还是来吃饭的,都亲切地称她为“老板娘”。
姑姑热情好客,对待来住店的客人像家人一样,嘘寒问暖。姑姑喜欢干净,客房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一丝不乱。住店,价格不贵,公平合理。走南闯北在生意场上打拼的人,风里来雨里去,他们来到镇上就在姑姑的店里落脚,也常把那里当家。这些客人中,大多数来自龙溪、草塘,他们以收米卖蛋为生。
逢至一三九赶集的时候,老远就会听见生意人的声音:“老板娘来一盘青椒炒肉丝,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外加一个豆腐汤。”那时候,姑姑比较忙活,她不但要照顾生意,还得亲自下厨。姑姑做得一手好菜,她炒菜时,姑父打算盘收钱,还得和店里的小伙计一起收碗洗筷。
在不忙的时候,姑姑会炖猪脚和花生汤给我们几个学生吃。那个年代,农村条件不好,吃肉的日子比较少。我和妹妹、两个表弟,还有在镇上教书的表姐,我们几个人围坐在桌旁,像极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不过,我们有点不太懂事,有时急于上课,嗅着闻着,不等姑父姑姑到桌旁,就各自在碗里盛了猪脚花生汤,一边喝一边等。姑父打趣我们,说我们一个个像下山的土匪。而姑姑却笑着说:“让他们吃吧,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补充营养。”花生猪脚汤,吃在嘴里,唇齿留香,而姑姑的话语在我的脑海里久久回荡。
姑姑自己不舍得吃,一边夹菜给我们,一边笑着看我们吃。她的笑容像阳光般温暖,她的话语像清泉一样甜,已经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了。
我把姑姑比作花,她清雅脱俗的气质,堪比一朵纯洁的花儿。她的家,一年四季都是花木繁茂。春天里,不但有名贵的牡丹花开放,还有那太阳花儿静悄悄地开又静悄悄地凋谢;夏天里,吊兰繁茂,还有那茉莉花悠悠地飘着清香……
姑姑家就像一个小花园,一年四季都能欣赏到花开。真应了那句话:花开富贵人家,喜气祥和。
二
初中三年,我常住姑姑家。姑姑除了做生意,她还养了两头猪,剩下的残汤饭菜正好用来养猪。她常常独自一人去割猪草,离家有点远的地方草肥。我想一起去,姑父对我说:“你好好读书吧,书里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姑父曾当过兵去过朝鲜,是个刚硬的汉子,可是关心起我们这些孩子来,倒像是婆婆妈妈。
我们学校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常在姑姑店里吃饭。还有一些单位的聚会,他们也会选择在姑姑家的饭店里。
姑姑饭店的灶台有三口锅,一口锅煮饭,一口锅炒菜,还有一口锅烧开水。灶膛的火烧得旺旺的,就像姑姑的生意红红火火。老远就能看见冒着蒸饭的热气。还能闻到蒜台炒回锅肉的香味。灶台后边的台子上摆放着几个盆子。小盆里有切成薄薄的土豆片,切成小段的葱,切成丝的瘦肉,切成末的姜蒜。那口烧开水的锅煮着大骨头,骨头汤里还有洗净切成块的白萝卜。大火煮滚大骨后,捞起沥干血水,清洗干净,再与白萝卜用小火炖煮。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的鼻子老远就能闻到一股骨头汤味。我和其他几个同学说:又有骨头汤吃了。对于我们住宿生来说这是改善伙食的时候,心里美美的。
遇到街邻右坊办红白喜事,街邻们都要来请姑姑当主持人。她一张巧嘴能说会讲,而且酒量还好。遇到陪同接亲的或送亲的宴席,姑姑巧妙周旋,常常会让那些不会喝酒的人都能喝上二两白酒,餐桌上一阵阵笑语不断。
只要逢到赶集,姑姑的饭店里总会有乡下亲戚带着小孩来玩耍。有时他们背篓里背点土豆,背点新鲜的蔬菜,但也有空手什么也不带的,隔三差五的来“看望”姑姑。姑姑抽空会炒上一两盘荤菜,或者下一碗肉丝米粉招待他们。他们很少有人付钱,一般都是吃完饭就赶场去了。在镇上,他们也算是姑姑的常客。姑姑面带笑容,不气不恼,一如既往的招待他们。
不管远近,说起姑姑,直夸她人缘好、为人善良、待人和气,而在亲戚朋友的口中更是称赞不绝。
三
有一次,我听见别人称呼姑姑为“阿庆嫂”。还别说,她真有点像。她为人处事不错,八面玲珑。不管是镇里的干部还是乡村的老人,都喜欢与她亲近。我们村里有两位老人,常把姑姑当亲生闺女看。逢到赶场,老人会背着背篓去姑姑的店里看看。姑姑再忙也会给她们上碗肉丝粉,让她们吃饱了再走。
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姑姑不仅只是做生意,还在结善缘。
后来,姑姑的饭店所在的地方,因规划调整,她只好重新在街上租了一个门面,起早贪黑地卖起早餐来。在她的努力打拼下,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时隔多年,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感觉人生迷茫的时候。就会想到姑姑,想起她的爱,想起她的善良,我便会振作起来,抛开烦恼。
姑姑已于今年的四月份离开了人世,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泪水已经在眼眶里转悠。在这静怡时光里,沾点岁月的痕迹墨浅一段往事的回忆。
她慈祥的笑容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叮嘱的话语还在耳畔,她勤奋的一生像一盏明灯,尽管人走了,那盏明灯依然亮着,给活着的人一片光亮,给挂念她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久久挥之不去……
文/李芳莹(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