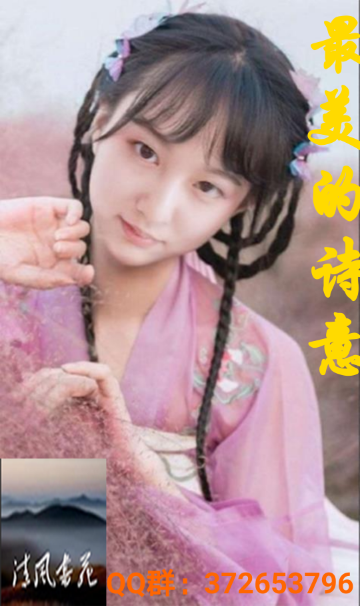【浪花】听佛语(散文)
【浪花】听佛语(散文)
![]()
一
面对浩瀚的黄海,在石岛湾一侧的赤山上,矗立着一尊世界第一大海神像,名“赤山明神”,是神,也是佛,人们都称“大佛”。
黄海鼓浪,推波击岸,耸峙于犬岸的赤山,抱住亿万年不息的海之花,但在石岛人看来,黄海如此喧哗,而山无回应,似乎少了“你情我爱”的情调。近处海不扬波的石岛港,千帆万桅,一幅动景,却不知谁人来吟赏,山风无韵,海潮单调,于是石岛人心怀惆怅,觉得那温暖的港湾,“自作多情”了一腔柔情蜜意。
时代和财富,一同给了石岛人,那是2003年春,一个超级大的臆想蓝图,就这样突兀而起,终于在和景惠风里,曾经蜗居在赤山深处的红门洞小山神,迤逦走出,矗立于苍山巅峰上,而且摇身一变而为俯瞰大海的佛神。从此,注目黄海,护佑一湾。
我喜欢每年去看佛神。无需购票入山,站在漂向黄海浅滩的栈桥上,扶栏举目,便可以赏读这本无字的“佛经”。终于,我被这尊明神的话打动了,一个声音说:无惧渺小!我知道这不是《佛经》的禅语,我想到了一句让我在自己的卑微面前矮小得不能看见自我的话:蚂蚁在白色的死海中穿行,无畏无惧。赤山明神似乎也在重复着这个句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佛语梵音。我喜欢耳畔响彻着鼓励的声音,美妙而动我心。
回家,再翻书,读散文家丁立梅女士描写这尊海神的文章《佛不语》,反而有了与她论剑黄海的冲动。原来她还是对的,佛不语,人在语。她的解读是“大爱无言,大音希声”。可我还是如鲠在喉,便再临佛前,闻听佛语。
“妈妈,”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站在佛足之下,将小脑袋仰向与天齐平,祈求地说,“我想把这个像摆在我的桌子上……”
孩子的母亲一手捂住了孩子的嘴巴,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惊恐,压低了声音,从喉咙里推出了两发炮弹:“胡说!”
童言无忌啊。我反而觉得小男孩比我这花甲之人更有博大的心胸。大,在他幼小的心扉里缩小了,一张桌子可以容纳得下一尊大佛。想起这些年,我始终心存“渺小”,处世慎独,自卑人微言轻,出语谨慎,常以“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以为处世之准则。面对小男孩,我觉得自己的确渺小了,渺小得甚至多少年不见自己的影子,唯有一个名字还存在。
这位母亲也自知在孩子面前失言了,便蹲下来,小声安慰着:“妈妈把那个从泰山请回家的‘男娃女童’抱着的人儿放到你的小桌上,好不好?”母亲的手很大,指很长,罩住了孩子的头顶,孩子马上蜷伏在她的怀抱里。
举目赤山,人反而轻飘飘的,似在云中,佛给我的不是压抑,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的振奋感。壁立千仞,叠翠染绿。脚下就是缠绵悱恻的黄海,海水湛蓝,如锦款漾。阳光铺洒,海水闪动着绸缎起伏的光泽,身后的赤山明神的金光也跌进了海水。哦,在这阳刚与绵柔的间隙里,佛占据着自己的位置。山巅之上,高耸戴天,资料说佛像高58.5米,是山拥了佛,还是佛坐了山,如此和谐,让我对供佛于此的人是创意感到惊叹。佛面东海,目光平和,厚笃持重。左手随意搭在腿上,右手臂抬起置之胸前,手掌向下。佛不语,何意?我想起了曾经去岱屿岛见到的“海不扬波”四个字,哦,原来佛手就是给这四个字做着无言的注释。这是岛上的渔人的一个心愿,心愿化作一只佛手,抚平的是万里瀚海的惊涛骇浪。这种力量给了他们塑造的佛像,为出岛耕海的良愿找一个寄托,他们相信这个想法一定可以成为真实,也让止步明神之下的人明白雕塑者所思。佛不语,佛意却在呢喃。我想了一句诗:“填平东海不扬波。”这个说法太狂妄了,精卫填海过,碎石枯枝岂可平渺水?我还是喜欢佛的手势所表达的境界,尊重自然,可以在自然里浮沉,才得精彩的人生,因为愿望是可以化为力量的。我的解,自信正确,我记得一语:佛性即人性。还想起与我的一位趣味投合的渔民朋友聊天时说的话,这尊“赤山明神”在今天才有了与人所想非常契合的可能。当初,我没有理解,这么政论性的句子居然出自他的口。现在想,他的话很深刻,石岛的渔船,几十年间没有出过事故,时代的科技,保证了出海人的步平履稳。佛界六道与现实世界,总有共同的点,未必信佛,但佛性人人皆有。我的目光回到那对母子的身上。母亲的手还抚摸着孩子的头顶,我突然想到了“开光”之说,这也是佛性,母性的光芒,只一个动作便诠释得如此清晰,母亲也是佛,佛性如母。极目远眺,海中渔帆点点,我相信,他们无论处多远,佛光都可直达,因为心中有一缕生活的牵挂,在他们温馨的家中,也写在了这静谧的佛光里。
这位母亲很年轻,染着金发。我告诫自己:不要以为这位母亲年轻就配不上“母性光辉”四个字。我想起了我母亲三十多岁时的一个动作,我的亲姐来看我,母亲就选了一处栀子花繁盛的地方,将我高高抛起。她是想告诉我的姐姐,她有多么爱我。只因我是母亲的养子,她要做这样不胜体力的动作?这不是夸张,是最深情的表达。
二
一阵轻雾徐徐漫上了山坡,从云层间隙透出的一道阳光射穿了雾,若绸缎一袭,似轻纱几片,嫋嫋羞涩,流淌入谷,曼妙裹楼。人在明神之下,时有绿树扑面,时有岑岩瞬现,阳刚的神,居然就像一首长调的婉约词,我只顾得欣赏,无心也无法读懂它慢条斯理的句子。但此时一切都在开口说话,有人说,这山就是半山半雾,分明是让人羽化成仙。此时,何处都是云霄玉殿。雾绕着山,柔抚摸着刚,相生相依,我们完全可以撇开山的地理性,雾的气象说,寻觅触碰我们心灵的意义。我想,这番景象是否就是一种说话的状态,或许就是欲言又止。举目去看,明神的唇吻显露出来,但并不呢喃。有些时候我们相对相视,久之,便感觉似在心语,这应该是一种得悟之境,恰好可以做静思顿悟了。
一对青年男女,在佛前相拥。我不知是否犯忌,但我还是觉得温暖了。我偷听了他们的对话。
“向下按着手掌,啥意思?”女的侧脸娇喘地问。
“按捺得住幸福。”小伙子绝对有着恋爱的高情商。
“那个词,叫‘按捺不住’吧?”显然女孩子是想表达亟亟心动,她说的是恋爱的心情。
我不知他们选择这个地方的目的,或许就是为了休闲,但这种表达,是有神作证的。或许他们就是故意说给明神听的,应该是。我们的信念,有时候与佛相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佛,就是人心人情的化身。明神的手势,是做了一个爱情的表达动作?我想一对恋人是这样看的。心平,却情感的波涛涌起,的确按捺不住。心波荡漾,按压不住,怎可按捺得住!年轻人拍婚纱照,喜欢海边,取“海枯石烂”之意。我觉得当下最要紧,起码看看彼此是否心动,是否心有灵犀。以后的事,是在于经营,而非盟誓。我不知此后是否有新人到这里拍婚照,但这是我见过的最美表达,我听到了经典的爱之语,细腻而含蓄。他们的爱之语,因佛而生。
其实,我不必跑很远来凸显我的存在。这么高的佛像,人在下面,形同蝼蚁,我突然觉得明神的从容微笑,给了我别样的解读,或许它就在对我说,我看见了你。那种慈眉善目,就是悦纳了我。我的心就像受到了点化,竟然安然无语,一阵低首沉默。我是无神论者,也不信佛,但我尊重一切信仰。我听说,当初倾33吨黄铜打造这尊佛的主人,也不是信佛的人,是俗家。他或许就是想创造一种神奇和博大。大的含义是什么?数学上无限大的概念,我们想不出大的程度。但诚心之大,才有震撼的力量。在我们的认知里,有时需要信仰特别的大,来包裹自己的渺小,用博和大,来扩展自己的胸怀,也许这才是这尊佛的“大”的真解。
一群游客的眼光都集中到佛手上。有人问同样的问题,有人说,这是心痛的样子。是啊,惊涛骇浪打来,折桅撕帆,将我们用筐土填充的堤坝码头一下子夷为海域,渺小的人,被卷进海浪,成为鱼腹之物,这些怎能不心痛如割。我举目看看明神,明神无语,又似在抿唇含悲,佛在语。有人说,那是佛伸手拿东西吃,或者是为我们俗人讨一包美食……这是个让人发笑的答案,一个孩子将手中的包装副食擎起。这样的答案并不标准,可这里并不需要标准答案,如果说有标准,那就是,佛在我们的烟火凡尘里,在我们的俗眼俚语里,在我们的童言无忌里。
游人在佛前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佛从来不会给游人的话写下“深刻”或者“肤浅”这样武断的评语,总是以微笑面对。这让我想起了一则问佛的故事。有人问佛:如何才能如你般睿智?佛回答说:佛是过来人,人是未来佛,我也曾如你般天真。我相信的是,一个心智聪慧的人,佛何时都可以与之对话的。佛界就是人生的境界,我们就是在天真里长大,所以我对那些有趣的俗解反而觉得温暖了,愚钝时,我们少的可能就是一颗温暖的心。
还有人面佛而叹:“踞为一尊佛,有多么不容易啊,风餐露宿,一个姿势摆到底,那手臂怎受得了,我真想给佛敷一叶解痛活血的‘筋骨贴’……”我不以为是个笑话,人世独有的同情心,让我也生出一腔悲悯情怀,真是人心可成佛,不期未来。
三
我曾经读过《张保皋传》,张保皋大约是我国唐朝时期的新罗(今韩国)人,他是行走在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劈浪者,也是赤山法华院的始建者。据说,原本的明神是他所造,藏于红云洞。神佛的样子没有改变,那只手就是表达着抚平海上风浪之意,可以想见,那时,中韩商贾之帆,遮天蔽日,赤山成了登岸的灯塔,也是心往的圣地。对佛,无所求,只有一只手的温度,一只手的千年不变之势。
如今的“丝绸之路”,走的是五洲大洋,靠的是坚船,载的是友谊,一个手势表达不出这样的含义。我所感慨的是“今非昔比”,佛手,倒成了“互联互通”的信号,似乎在说,这里风静浪平,这里安然无恙,这里风景独好。
我也随着游人端坐在佛像的脚下,突然想到了“人人皆可为佛”的话,形式上的,也有着瞬间笃定的意念,人生的反思,往往是某时某地的顿悟。我的很多想法,都在神佛像前突然静心求取而得。人们并不忌讳在佛前做着自己的事,吃东西,拍照,交头接耳,明神无语,都容许了。也有人在双手合十,可能在许愿吧。我不知这里是否可以不交香火钱许愿是否管用,但我马上觉得自己好笑,许愿是将心中所思诉诸意象的行为,所谓心诚则灵就是这样,不必在乎是否奉上了香火。况且遵守山林防火规定,这里的明神从来不在乎香火,只要有体力登山而来,他都低眉敛目,笑容可掬,嘴中似乎在念叨着:欢迎,欢迎!
参拜的形式是无拘的,随心可意就行,我们可以去解读明神的无声之语,也可以面对明神说出内心的话,困惑,挫折,悲伤,失意,无奈,心愿,理想,哪怕是一个并不在意的想法,佛都在听,也不会泄密给人,用不着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样的咒语,佛永远是一个让我们放心诉说的好听众。再看那佛手,我觉得是在做着听人说话的手势,好像在说,我在听,放心吧。学着佛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吧,佛的动作给了我这样的启发。
每个人面对佛的解读和感悟是不一样的。我对佛的善眉慈目、微微做笑的神态有了联想。面对的大海,或波光粼粼,或惊涛接天,佛总是一个神态,不惊不惧,笑看骇浪,真有以笑抱怨的姿态,笑是可以解释所有坚强情绪的,也许我看到的是假象,但我长时间和佛对笑,它已经感染了我。
拜佛是否灵验,也可能出现巧合,站在佛前表愿的一刻,可以给心灵宁静的瞬间。任何事的转折转变,神灵是无法左右的,从来都与人事有关。佛在山巅,日复一日,笑对红尘万丈,不管我们是否到来,佛就在那里,无言无语,用心的人,可以读出佛声,心中有佛,心底存良,人就有了佛性。象征的意义大于现实意义,这是我们对佛的清晰判断。
人的生活,并不拘泥于红尘,红尘之外,还有一个倾听的地方,就是赤山明神佛像前。读懂自心的,还是靠自己。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我们顾不得停下来反思一下,难得有一尊佛像,它告诉我们要面壁而思。“清风明月有禅心”,这个境界并非一般人可以彻悟而得,还是应该有一个氛围,到佛身边来吧。
听佛语,就是倾听自己。佛不语,自己的心扉必须打开。
和我的朋友说起赤山明神,他强调说,每个晨,是第一缕阳光普照着神佛。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世间本就有永恒的光芒,就像我们每个人心底都会接纳阳光一样。神佛,只是我们创造的一个迎接阳光的人。
2020年9月12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
问好老师,遥祝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