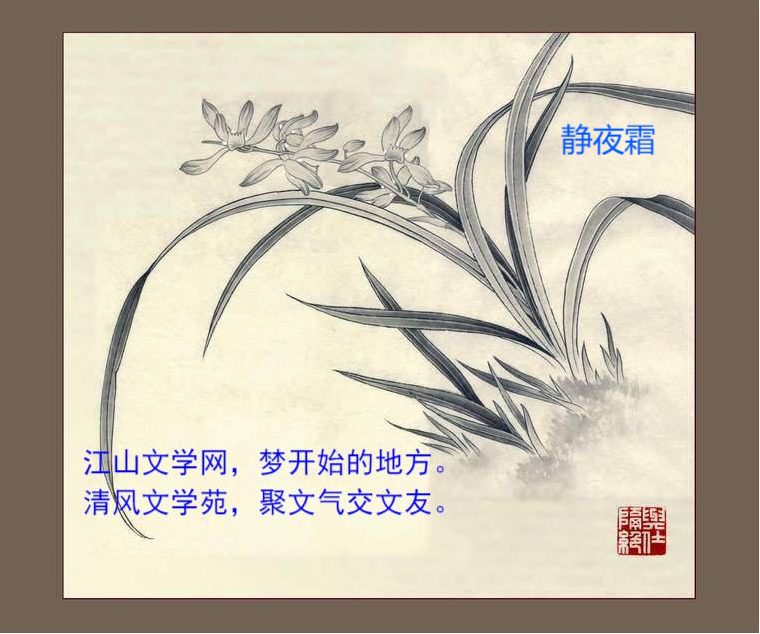【读名著·传经典】【凤凰】读名著,传经典—从儒林外史说起(赏析)
【读名著·传经典】【凤凰】读名著,传经典—从儒林外史说起(赏析)
![]() (一)
(一)
知道《儒林外史》,是从中学课本里面那篇《范进中举》开始的,那个考上举人发疯的形象,像一枚钉子,楔进了我的脑海。因为受到“反向激励”,怕自己成为第二个范进那样的人,所以养成了日后对权势疏懒的性格。
直到头上长出白发,在人世间历尽波折,才知道自己当初那些看法是不对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由我们大家组成的,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把应该争取的权力拱手让给别人,那就不要怪别人在侵凌你的权力。
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观点,而不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当时的观点。在吴敬梓生活的年代,是皇权的年代,是封建社会走向巅峰之后,正在走下坡路的那时候。那时候,皇权来自上天,来自皇帝的父辈、祖辈,而不是人民,于是,不存在争取权力的问题,只存在向权势谄媚,或者疏远权势的问题。
显然对于今天的这个时代来说,《儒林外史》已经过时了。那么,我们来探讨这样一部已经“过时”的小说,还有意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检验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就是时间,几百年之后,当我们仍然能看到这部作品,就说明了它的价值。
那么它的价值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它的价值是,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发展之路,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我们的作品应该谋求的发展方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儒林外史》都以“另类”的面貌存在。因为从《国风》开始,中国作品就强调“哀而不怨”,显然,进行辛辣讽刺的《儒林外史》,并不具备这一“美德”。那么,是什么样的环境,导致作者不顾一切,打破长久以来形成的“禁忌”?为什么它又受到人们的追捧的呢?
中国小说源远流长。
《庄子》被人们称为小说之祖,里面饱含哲理的寓言故事,开小说写作之先河;时间来到唐代之后,《柳毅传》、《虬髯客》等志怪传奇小说,开始走向前台;宋代的《太平广记》,里面收容了无数短篇小说。然后,经过千年的积累,到了明清时代,小说创作迎来了爆发。
而小说创作的爆发,是有几个因素促成的。
第一个因素就是时代的发展,让个方面的力量都在增长,让一直担任群众演员的“草民”,正式登上国家生活舞台,使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有了土壤。
如果我们把秦始皇的政治体制与明朝做一个对比的话,会发现皇权的结构,比过去不知道复杂了多少倍。秦始皇时候,政治结构几乎就是单纯的一言九鼎:皇帝下面也有丞相、九卿和各级官员,但那都是皇帝的手和脚,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于是,当皇帝英明,整个国家就强大而威严,当皇帝昏聩,大秦帝国就二世而亡了。
当然,权力结构简单,所以效率就高;而结构复杂,效率自然就低。于是,秦始皇能完成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修长城、建驰道、开疆拓土等一系列壮举。而后代君王,虽然也有不少胸怀大志的人,却难以达到他的高度。
明朝时候,甚至从西汉开始,国家政权形式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皇帝、皇后和朝臣,三者形成微妙的三角形,互相制衡。那时候除了汉武帝乾坤独断之外,皇帝的权力都要受到限制,连中兴之主汉宣帝也不例外,要受到霍光的“威胁”。
东汉时期,开国皇帝刘秀,把郭胜通封为了皇后,而不是念兹在兹的阴丽华。除了阴丽华的贤惠、谦让,还在于东汉建国之初,他需要大家族的支持。开国皇帝尚且这样,后代皇帝就不用说了,除了帝权、后权、朝臣,在东汉还有外戚、宦官等等,让权力在各个利益群体中不停妥协。
而这种情况到了明朝,就更明显了。
那么,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多妥协?一个人一言九鼎不好吗?
一言九鼎当然很好,但越到后来越做不到。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外族、生产力,都在增长,方方面面的力量都在增长,人就必须得向这些力量妥协——程度有多有少,但不能毫无顾忌。
今天,让我们回到自己家中,看看我们的家具家电、出行工具,就知道咱们这个国家工业生产的社会协作到达了什么程度。
例如最常见的电视,里面有芯片、外面的屏幕,电源线用的电缆,信号线,网络线、机顶盒等等。沙发看起来比较简单,但制作沙发需要的各种机器,各种材料却一点儿也不少。至于交通工具,那更需要修建道路,建设桥梁,需要养护等等。
明朝的时候,生产力当然没有这么先进,但火器、枪炮的出现,大型海船的建造,说明生产力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资本的力量,成为重要的力量。
资本的力量在增长,文化的力量就在增长。
秦朝时候,除了叔孙通之外,几乎听不到什么文人的事迹;到了两汉、唐宋时期,文人开始受到重视;而到了明朝,东林党人已经成为重要力量。
国家各方面的力量在增长,外患的力量也在增长。
始皇时候,外患基本上就是胡人,也就是匈奴,而那时候的匈奴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直到冒顿单于,匈奴才像个国家;而到了明朝时候,不仅有蒙古,还有日本、英国、荷兰、缅甸,当然还有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满清。
这些外患的实力,远超过当时的匈奴。这时候,对于外患,已经不是简单的征服与打败的关系,而是要学会共生。
所有这些力量,必然会提现到最高权力结构当中,使得权力结构变得复杂。而结构复杂带来的好处就是,各方力量的制衡和稳定。于是,从隋朝之后,中华大地上,每个王朝都有二三百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皇权也在增长,因为皇权经营的范围,覆盖的区域,影响的族群,管理的深度,比大秦帝国时候要复杂很多倍。仅以教育和文化为例,从“焚书坑儒”政策就可以看出来,秦朝是相当粗蛮的;对于外族人,始皇帝也主要是镇压为主;对于经济,他的建树也不多。由此可见,当时的皇权,还是比较单一的行政权力而已。
而从西汉开始,由于匈奴的强大,外交和军事面临的局面变得复杂;由于累世的王侯,土地兼并,盐铁专营等问题变的严峻;由于文化的繁荣,以及异域文化的输入,人们的思想也发生变化。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皇权做出应对。体现出来就是君王或者君王的代理人,更会妥协,更懂得平衡之术。
为什么要妥协?因为这些力量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不论你过分打压哪一种力量,都会引起失衡,带来塌方式影响。
东汉不重视农民,农民开始起义;唐朝末年,皇帝将清官丢进黄河,国家立刻就完蛋;宋朝不喜欢武将势力独大,于是整个宋朝就软骨头;满清不重视生产力发展,对江南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打压,结果造成工业革命迟迟无法来到中国,结果被西洋人拔了头筹……
社会发展层次越高,均衡就越重要。
应该说,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增长,但皇权力量增长的幅度是最小的。因为经过无数代人的顶层设计,皇权改进的地方已经非常小了,但其他力量增长的空间却近乎无穷无尽。
这些力量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冲突,而当冲突的力量外溢时,底层的草民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原因很简单,当大家都想扩充自己力量的时候,必然会开发新领域,而“草民”,就是最庞大的宝藏。而最能充分反映“草民”生活的艺术形式,小说,自然就受到了追捧。
从《三言两拍》到四大名著,都是因为扎根在民众之中,从而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这些作品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
除了时代的发展,给了小说发展的机会,第二个影响因素是,传统的道德力量发生了裂缝,以前围绕君子展开的中华文化,开始逐渐为“草民”服务。
大家都知道,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道教和佛教,虽然在形式上红红火火,但是,与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儒教相比,在影响力和对社会贡献来说,都差得太多。
在儒学里面,一个重要思想是“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是,立德立言立功,就成了文学创作者的主流。
立德立功,自然都是“君子”的事情。
当然,儒家并没有拒绝“草民”发声。在《国风》里面,就有不少篇章是普通民众的声音,例如《伐檀》、《硕鼠》等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都有写劳动人民的诗歌例如李白的《秋浦歌》(其十四),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描写劳动人民的名篇。
然而这些诗歌,能真正深入进入到“草民”心里去吗?而那些知识分子对“草民”的同情,又会有多大作用?要知道,今天还有无数人对诗词不感兴趣呢,何况是那时候,“草民”基本上都是文盲,活着就是挣扎,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哪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诗词?
这种情形一直发展到南宋,终于出现了转折。
世间的事情总日中则昃,月盈而亏。南宋朱熹倡导的“灭人欲、存天理”,把儒家的教义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让儒家教义开始被人普遍怀疑。
与以往李白那样的狂生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不一样,这次是无数人的怀疑,把名利二字放到最高位置,把男女之间自然情欲描绘成万恶之源,绝对化的后面,就是猛烈的反击。
然而,南宋理学又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就是站在道德的高度说教,又怎么会错呢?
理论上无法打倒理学,一些人开始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发展。《一刻拍案惊奇》、《再刻拍案惊奇》,就能明显看到其中的痕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猫要叫春,谁能挡得住?
除了内容贴近生活,表现形式也更加贴近生活。明清小说,基本上都是章回体的,一个重要的写作方法就是“做扣”,也就是留下悬念吸引大家下次来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这样的。而且,比起需要一定欣赏水平、文化功底才能理解的诗词,小说简单易懂、贴近生活,更加喜闻乐见。再加上职业说书人的讲评和演绎,小说迅速就能占领“草民”的思想战线。
明清小说,已经是真正的小说,而不是唐宋时期,范围仅限于民间传奇故事,或者神话传说方面了。
第三个因素是,文人自己突破的需求。
唐诗宋词元曲,两汉文字,加上《国风》、《离骚》,几乎把诗词歌赋、文章典籍的光芒都夺走了,后来人不要说突破,就算是追赶先贤的脚步都很困难。于是,后来人想要突破,必须寻找新的途径,而能充分表达个人思想的小说,显然就是最好的形式。
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超越自我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二)
《儒林外史》里面有很多细节描写,手法娴熟,描写生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而其中一个最大的细节,就是读书人对功名的痴迷。
读书人把功名看成了命根子,普通人把取得功名看作是鱼跃龙门,国家以功名为标杆,衡量天下英才。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里的人民,本来就应该是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的,可是因为功名二字,统统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
不是科举制度不好,不是功名不好,而是国家选举人才的标准不应该如此单一。
在这方面,明朝的统治者和满清的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获得了不同的结果,得到了相似的结局。
火器,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但是冷兵器时代走向热兵器时代的标志,同时还是用头脑补偿体力差距的良药。不论健壮或者羸弱,在火器面前,基本上做到了人命平等。
从明朝,或者从元朝,甚至从宋朝开始,火器在中国就出现了。根据暹罗的历史记载,最早的火器是从东方贩卖到西方的,是后来技术落后了,这一过程才倒流过来。
而在火器的后面,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集中体现。就拿最早的火枪来说,制造枪管的钻头,锻造钢材的高炉,造型奇怪的扳机,做顶针用的弹簧钢。由此还需要铁矿、煤矿的开挖,水路、陆路的运输等等。
一把手枪所影响的产业,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而这就需要整个社会协作起来,在这种社会协作的背后,就是新生的力量。
面对新生的力量,明朝人选择了静观其变,或者就是放任自流。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但朝政并没有出现大的偏差,皇帝的作用,主要就体现在平衡各方面关系上。
而满清面对新生的力量,采取的手段是野蛮压制。很多人都说,满清十三帝,个个都很勤奋。这些皇帝确实很勤奋,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勤奋,才造成后来大清国闭关锁国,关闭了海防,阻断了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让自己成了夜郎自大的典范;因为这种勤奋,明朝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工业化生产的先进生产力,被扼杀在摇篮里;因为这种勤奋,中华民族迎来了灭顶之灾,差点亡国亡种……
很显然,明朝和清朝的统治者的办法都不算高明。一个太被动了,就是混吃等死;一个太武断,眼光还停留在汉唐时期,不知道这个世界早就发生变化了。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比起统治者的迟钝,或者说野蛮压制,知识分子反倒觉悟的比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