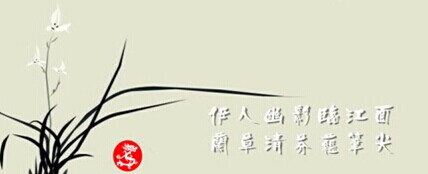【江山·好声音】【流年】云霞深处好声音(散文)
【江山·好声音】【流年】云霞深处好声音(散文)
![]() 一
一
彩云之南,五彩的山路上,走着一位壮年汉子。人们叫他“山地”,因为,他从小生长在这苍茫大山里,长得和崇山峻岭一样结实。小时候,妈妈喊他“小石头”,他像山间风吹雨刷的小石头一样顽皮。转眼间,已经是六十岁的人啦,他被风雨冲刷成了老石头,脸上有了纵横,眉宇间有了夹皮沟,风清雨洗,这块老石头,不再光滑润泽,却在去除了无数杂质之后,更加纯粹,更加坚实。
山地,是土生土长的云南汉子,有个写在大学毕业证上的大名“朱华胜”。流年社团的朋友们,都喊他“山兄”,极个别时,也会有人想到他大名的谐音:煮花生。花生是极易生长的植物,有土壤,有点水就行。没有细致的考证,没有家谱流传,可四围里的人都说,地处云贵川三边的曲靖朱氏,先祖来自美丽富足的江南。朱洪武的大明朝开国,皇城设在虎踞龙盘的江南腹地金陵,封开国功臣沐英镇守彩云之南。其间,分三次派遣数十万江南军民戍边屯田,也有皇族龙子龙孙,封来云南为王称侯。山地不曾向江山流年的文友说过他的家世,不过,有野史流传的地方,一般都离真相不远。
一条溪流,如果只是在自家门口流来淌去,那只能被称作可笑的沟渠,只有奔向远方,走向辽远,才能成就大江大河的美誉。我想,山地的先祖们,正是以这样的气度,离开沃野平原,南下湖广,翻山越岭,渡水涉川,从水韵江南,来到云霞深处,开拓云南、垦殖云南,使这蛮荒之地,雪山高原,有了与中原一样的文明开化,一样的残阳暮烟。
年近花甲,二级调研员山地,在中原已经可以被称为老汉。他可以选择退居二线,在窗明几净处,一边览报,一边品茶。很多人,已经不再朝九晚五地打卡坐班,他们白天钓鱼、下棋,砌长城。晚上,则或品酒赏月,或漫步林荫道上,兴致来了,还可以邀个女伴舞上一曲,在歌厅吼上一嗓子。可这个山地傻啊,他哪里像个坐办公室的官员?骨子里裹不住的文人气,始终激荡着为国建功立业的豪迈。就像晚年还要仗剑从军的李白,就像白发皓眉还要跨马戍边的辛弃疾,就像暮年梦里都要金戈铁马入冰河的陆游,山地,选择折根柳枝做拐杖,进入深山去扶贫。
党中央发起扶贫攻坚战,他就是一往无前的过河卒子。他要用偾张的朱色血性,让红土高原更加红艳;用浓得像盐一样的汗水,让高山大川里的贫困农家生活得有滋有味;他要用党的真情,政府的厚爱,抹去高原各族群众忧愁的泪水,展开欢乐的笑颜。而他自己情愿把生活咀嚼成青涩的橄榄,做一个悬壶济世,专治贫病的医者,专赶穷鬼的钟馗。
差不多将近十年前,我在江山流年结识了山地。当时,我就想:一个县处级干部,不在政坛官场上爬升用心思,却来这种文学网站玩野狐禅,不是悲天悯人,大智若愚,就是冥顽不灵,真呆真痴。那时流年申酉大哥还在,我在社团排名二哥,官场上可称县太爷的山地,却排在我们两个“大国工匠”之后,成了敬陪末座的五阿哥。差不多十年光景下来,他不矜持,不造作,整日乐呵呵地敲键盘,真是性情中人,有苏东坡的不羁,陶渊明的风格。
山地这天去的是白云深处的狼杂村。“正午,峭壁张着嘴,似乎要把一团正在洞口睡觉的白云吸进去。”他在这个半山腰上的洞口,听到一个故事。这大山里一个胡姓彝族女人,从娘家返回村里,居然就在这个山洞里勇敢地独自生了孩子。“一声婴儿啼哭,十几只黑尾麻花鸟从洞里掠出,穿过白云,翅与云摩擦的声音,和着婴儿啼哭声,击碎了这一方安静。”
这个勇敢的母亲,生过孩子,就像没事人一样,抱着花蕾一样的新生命,继续踩着云朵上了山。“听到她的讲述,内心极为震惊。”极为震惊的山地,在这个山洞边想了很多很多,那一刻,他就像是面壁的达摩老祖一样沉默。
中原许多人的眼里,云南自古就是不毛之地,蛮夷之乡。其实,这里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开远出土的腊玛古猿化石,距今1400万年,禄丰古猿距今800万年,已经能够直立行走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元谋人比中原的北京人、蓝田人,都早了100多万年,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人类。远古人类的孕育生产是原始的,随便一个山洞就是接生的“医院”、随便一块容身的土地就是产床。可这是二十一世纪了啊,彝族大姐,还继续着元谋人的生育模式。历史的深厚与浅薄,生命的崇高与卑微,生活的艰难与苟且。这一切,激荡着山地的心。
多年之后,山地的散文《挂在白云上的村庄》获得江山文学绝品。这篇绝品文,记述了他行走在这大山间的故事,他将山路带给山民生活的不便,带给山民生活的艰辛,记在了心间,并不断拷问自己执政为民的灵魂,终于,这山间的羊肠小道,被他走成了柏油大道,挂在白云上的村庄,也沐浴到了党扶贫政策的阳光雨露。
“进入村子,村道硬化,水泥路面。村子通水通电通路,路面宽敞,院子宽敞,有的停着小车,农用车,也有的停着摩托,也有马车牛车。院墙角,都栽有花草。房前屋后,都种有水果树。面前这家,种着一棵苹果树,果实累累压弯枝头,苹果红得像刚才路过的红沙坡样的。”
山乡脱贫,红土高原上彝族人民载歌载舞的幸福欢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声音。
二
他在山间走着,牵着风,带着云。在寂静的大山里,于是就有了风的声音,云的声音。作为中国边陲的处级干部,他工作、生活在基层数十年,远称不上风云人物,然而,在天高路远,难见庙堂之高的贫困山村,老乡们就是从这些基层干部的脸上,辨识风向,猜测云雨。
作为一个旅游者,我不止一次去过云南。早年,坐在大巴上,透过肮脏的玻璃,在总也走不出的大山里,总是见得到沟沟渠渠,它们都很浅,它们都走得急,它们都冲击着拦路的石头,湍急、匆忙、毫无章法,就像是一架不曾调试过的破琴,发出嘈杂、混乱、极不和谐的声音。因此,我能体会到山地作为一个下乡扶贫干部的艰辛。
今天的旅游者,来到彩云之南,奔去的打卡地,多是昆明、大理、丽江和香格里拉。他们在五百里滇池放歌,在茶马古道跳跃,在蝴蝶泉舞蹈,在泸沽湖赞叹走婚部落的家乡,美得就像一块蓝宝石,而香格里拉的白水台、纳帕海、松赞林寺,更让人觉得走进人间天堂。而他们浑然不知的是,云南94%的面积是山地。云贵高原独特的高岭大川,隐匿了无数的贫困山村。它们与现代文明的差距,不仅仅是时髦女郎的滚筒洗衣机与老阿妈捶衣的棒槌。
“四月中旬的一天,艳阳高照麒麟大地,上午十时,我来到麒麟区三宝街道彝族寨子长坡村李仓家……客人的到来,李仓很开心,来到院子中央,吹起自制的乐器唢呐。他妻子从厨房走出来,一身漂亮的彝族服饰,笑眯眯的,伴着乐,欢快地跳了起来。”
这一天,山地是去探望已经脱贫的彝族汉子李仓。长期的结对扶贫,小李和城里来的老朱,已经成了好兄弟。今天他和妻子高兴地用唢呐和舞蹈,欢迎帮他们走出贫困的贵人。他家新盖了楼房,外墙全部贴灰白色瓷砖;他家新盖了猪圈,一头头猪滚圆;他家还买了面包车,要在奔小康的路上,跑得更远。
“李仓一脸的知足,说,政府很关心我,不管养殖还是种植,帮了大忙。我自己深有体会,现在政策这么好,作为一个农村人,不富裕只能怪自己,十穷九懒啊。只要敢于苦,哪有不富!阳光下,他说话时一脸的自信。”《长坡村的彝家汉》是山地在他的散文中记述的,又一个与山民结对扶贫的故事。
李仓发自内心的自信,是因为他看到了朱组长同样发自内心的坚定。共同跨过小康的门槛,在奔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党和政府把管教书、管体育的文体局领导干部都派进了大山扶贫,他从朱组长的脸上看得出,党和政府是真心真意地要扶持大山深处的彝族兄弟发家致富。
李仓家原来是这个村子最贫困的人家,李仓的父亲双眼失明,母亲也带残疾,艰难地生养李仓兄弟三人,李仓是最小的儿子。两个哥哥上学,他们家是村里最贫困的四户特困户之一。李仓终生难忘。父亲病了,让这个过得本来就很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家里只有几碗豌豆。村里大喇叭响起的声音让李仓心痛,仿佛被麦芒刺入。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喊:李仓家来村上,给你们十斤苞谷过冬。
穷困让人耻辱啊,忆及此处,总会让他有锥心的痛。不过也是这屈辱的过去,让他发奋脱贫。
“脱了贫的李仓,很有自己的想法,他向生活要质量了,按他的话说就是要过得有滋有味。他把家里打整得整洁干净,安了水箱,一家人随时可以洗热水澡。他家院子太大,他规划了一片花园,不仅种花,还种上白菜青蒜和大葱。长坡村委会书记对他说,李仓,你的生活有品味了,是我们长坡村人学习的榜样。”
临别,李仓眼里带着泪花向山地表示:朱组长,在脱贫的路上,我一定不会好了伤疤别忘了痛,一定坚持勤劳致富,绝不走贫穷的回头路。
山地欣慰地笑了。他告别已经富裕起来的李仓,继续走向白云深处,大山深处,那里,还有更多、更穷的李仓需要听到党的声音,政府的声音,需要召唤他们一起走出贫困,走向共同富裕。
三
他在山间走着,扯着闪电,顶着雷鸣。在寂静的大山里,于是就有了电的声音,雷的声音。
云南地处亚热带高原,人们都说这里四季如春,它似乎没有江南那样四季分明。曲靖的春天,不像江南那样有着细细密密的杏花雨、桃花雨,一阵阵细密的潇潇声,就能从雨巷里招呼出一千把,一万把油纸伞,油纸伞下是美丽、灿烂的笑脸。高原的春天是干燥酷热的,她有时就像一只炽热的煎饼锅,能将大山烤出些焦煳味。这里永远只有旱季与雨季。在旱季,都是干打雷,不下雨。云南傣族,在旱季过泼水节。而在雨季,山间小径会变得异常泥泞,在毫无遮掩的山谷中很容易就被淋成落汤鸡。那些原本乖顺的季节河,在此时就异常地湍急汹涌,像是奔突下山的大蟒蛇。还有山脚下的低洼处,此时就成了可怕的泥潭和不可测的陷阱,而隐藏在山路上的野草、藤萝、荆棘、刺棵,就像是山匪、刺客一般,给攀山者以生命威胁。
我们不知道山地在大雨滂沱时,是否跌进过泥潭,不知道在崎岖山路上,是否被藤萝缠绊,不知道他在进山的路上,是否遭遇过危险。他不曾说过,他给予人们的总是坦然的笑脸。
敢于进山扶贫的,不仅仅要有智慧、有知识,还要具有临危不乱的坚强信念。
进山扶贫是一个光荣的事业,也是个艰难的事业。扶贫攻坚中,山地遇到了李仓这样不甘贫苦,立志改变自己,改变家乡面貌的血性汉子,也遭遇过躺倒不起甘于穷困的懒汉。
当他询问乡亲们有哪些困难,需要哪些帮助时,有要政策的,有要资金扶持的,有要学技术的,有要试图自己创业的,山地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气度,为他们一一作答,也用实际行动为他们穿针引线。
山地在大山里,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说:朱组长,我就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我不要苞谷的种子,我不会耕作。我也不要去放牧牛羊,跟着它们漫山遍野地跑,太累。我也不要钞票,大山里也没什么好买的。你发我个婆娘吧,我需要个老婆。懒汉的无赖,引来山民们的哄笑。山地听了有闪电在眼里跑,有雷鸣在胸腔里跳,但他还是和颜悦色地告诉懒汉:姑娘不嫌穷鬼,就怕懒蛋。送走了穷鬼可以翻身,而懒蛋一辈子都会穷鬼附身。哪个姑娘会看中一个懒蛋?你要老婆不难,赶紧地拿起锄头,去散散你的一身懒骨头。山民们一起为朱组长鼓掌。懒汉趁着云朵遮月,躲进了草窠。
他在山间走着,披着阳光,携着雨露。在寂静的大山里,于是就有了阳光的声音,雨露的声音。
他在山间走着,嗅着花香,闻着竹绿。在寂静的大山里,于是就有了花开的声音,有了竹子拔节的声音。
他在山间走着,不再一人独行,身边有了几位伴随的年轻姑娘,那是他年轻的同事们。他们一路欢笑,一路歌唱。老石头,带着她们,送走了穷鬼,扶持起一个个富裕的山村。于是大山里有了笑声、有了歌声。
他在山间走着,走得无比开心。因为,他是在由大山走向平原,走向一马平川。这么多年来,他将一条山间的崎岖小径,走成了笔直的康庄大道。他给山里的乡亲们,带去了党的声音,政府的声音。他给山里的乡亲们带去了党和政府坚决消除贫困的决心,他给党和政府传递了山民们坚决消除贫困的信心。他将一条山径,走成了一条洁白的哈达,一条连接党和人民的纽带。
在退休之前,老石头终于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初心答卷》。这份答卷,刊登在江山文学网站,也登在他家乡的报刊上。
他在这份答卷里,这样写道:我不得不说,曲靖的减贫,在云南,乃至中国减贫史上,是富有特色的,作出了重大贡献。“三联三争”“五面红旗”“爱心超市”“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县级项目库建设”等曲靖模式,对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借鉴作用。
这场脱贫攻坚战役,异常艰辛,惊心动魄,从牯牛之巅,到石漠化的攀枝嘠,再到十八连山;从多依河畔,辗转凤凰生命之谷,连战龙海山林;从朗姆山,到旧县香炉山,再沿罗小村至珠江源头……曲靖大地战贫斗穷的壮怀激烈,贯穿每一个年头的日日夜夜,不眠不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曲靖光荣完成使命,八十多万人脱贫,二十万人挪出穷窝,走上了富裕的幸福之路。
文中“不仅仅是时髦女郎的滚筒洗衣机与老阿妈捶衣棒槌;有闪电在眼睛里跑,有雷鸣在胸腔里跳;披着阳光,携着雨露,嗅着花香,闻着竹绿;”语言美的一摊糊涂,我已经把它们都抄在了小本本上。
前辈这二个当得相当了得,之前的大哥的身影还未退去,三弟又隆重上“市”。“他将一条山径,走成了一条洁白的哈达”艺术性极强的语句,充分的表达了山哥的一路艰辛和成就。
前辈真是为江山的兄弟姐妹操碎了心啊!问好前辈,夏日安康!
灵魂对晤、以心悟心,逝水的时光变得更丰盈和饱满。
善待别人的文字,用心品读,认真品评,是品格和品位的彰显!
我们用真诚和温暖编织起快乐舒心、优雅美丽的流年!
恭喜,您的美文由逝水流年文学社团精华典藏!
感谢赐稿流年,期待再次来稿,顺祝创作愉快!
二哥写文,汪洋恣肆,胸中似有百万兵,这就是气魄,一般人真没有。学习二哥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