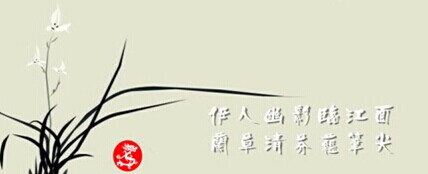【丁香】一份担当的思考(随笔)
【丁香】一份担当的思考(随笔)
家里看家护院的阿黄,产下七只幼崽,毛茸茸肉嘟嘟惹人喜爱,给家里也带来了生气,一到礼拜天,村子里的小孩三五成群,跑到后院,要逗小狗崽玩耍。由于缺奶,小狗崽十天半月眼睛还没睁开。每当阿黄钻进窝里,小狗崽像上了战场的士兵,匍匐前进,抢占先机,吮吸奶汁。虽双目紧闭,它们嗅着气味,凭着感觉,你争我抢,直到奶水吸干,挺着圆滚滚的肚子,爬向自己喜欢的墙角,打起鼾声。
随着一天天生长,阿黄的奶水赶不上崽子的需求,女儿便从网上买了羊奶粉,补充营养。每天早上和下午,我用温水化开奶粉,装在奶壶里,给它们一只只饲喂。阿黄不领人情,除按时吃食外,其余时间在野外逍遥,不管崽娃,成了没王的蜂。有一天它竟然带着相好(崽子的生父)回家了,看似又要寻欢作乐。小狗崽刚刚满月,它就忍不住寂寞,又想怀孕生子。我心里那个气不打一处来,地里的农活忙得我精疲力尽,回家把歇一歇的时间都用在照料狗崽身上了。七只小狗娃在我的精心喂养下,睁开了眼睛,隔三差五我给它们洗洗澡,已在地上像滚绣球一样行走了,可招人喜爱呢。在没有找到养户的情况下,难道又要产下一窝吧。气急之下,我把阿黄拴在窝边,我让你去潇洒!生崽不管崽还不如不生的好。
由此想到了一些题外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普遍不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去学校读书就是混年龄,混大点了就能干农活。回家接父母的班,镢头、铁锨、架子车,翻土、拉粪、扶犁把,传统观念束缚着他们的思想,老鼠生儿打地洞,念书有何用,实实在在挣生产队的工分,只要年底结算不短工日,还能使换(分配)百十块钱,过个欢庆年呢。在这种意识的导向下,顺其自然,放任自流,耽误了孩子的学业和前途。
星期天帮家里干农活,放羊、拔草喂猪、拉土垫圈,家里做的活都是孩子干的,父母高兴。有的家庭为了节省几块钱的学费,强迫孩子辍学,小小年纪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家庭劳动力多,挣的工日就多,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父母红光满面,气大财旺。院子里盖起了小楼房,在社员群里趾高气扬,走路仰头挺胸,吃穿住行样样走在人前头,遇事吆五喝六,过足了嘴瘾,潇洒了半生。
而有些家庭,为了供几个孩子念书,拉了不少外账,但他们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不会让孩子挨饿受冻,在他们的心中,供养孩子好好念书,就是希望。我们村子里的老王,人称王好人(外号)是生产队里的勤劳人,接人待物、说话处事有分有寸,但凡村子里谁家有事,他不图报酬,一帮到底,婆娘伙里的“出气筒”,青年群里的“娃娃头”,一位没有脾气的热心肠人。家里三个孩子他和妻子疼爱有加,知冷知热,常常鼓励孩子们多读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大儿子考上了大学,家里一贫如洗,为借学费,老王俩口跑东跑西,恨不得给人家下跪。要借几千元在过去谈何容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富人看见穷汉躲着走,穷人想帮没有能力。政府了解到他家的实际困难后,动员全乡机关单位和各村村民小组,捐款资助,顺利上了大学。一年后,二儿子又考上大学,遇上了党的好政策,申请了无息贷款……
儿女争气,父母脸上有光。他老俩口和以往一样,依然勤俭持家,依然穿着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翻新衣服,依然吃着粗米淡饭,过着不与人争,与人为善的生活……
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农村家庭承受着最大的经济压力。首先,得在城市有房、有车,才有条件谈对象。房子车子已负债累累,加上天价彩礼,更是雪上加霜。农村父母苦干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房,苦、愁、累压在他们的肩膀上。老伴变成了孙子的孙子,老头在乡下搭泥(打工),全身心扑在挣钱上,就这样也满足不了孩子们的心愿。
过去吆五喝六的壮年,已白发苍苍,再也没有敢闯敢干的精力了,他们看够了儿女的白眼,世道炎凉,未曾想老了老了反到被儿女逼上梁山。这口道不出的窝肚气憋在心里,不敢给别人说,不能给亲戚讲,吃饭不香,睡觉不安,像钻在风箱里的老鼠,肚子鼓的圆圆的。
受尽了别人的冷漠,过着清贫的日子,他们的孩子却出奇的优秀,考进大学堂,接受着高等教育。虽然为学费生活费费尽了周折,一出校门便成了厂矿企业的抢手人才,借贷很容易的就归还完了。婚姻不用媒人,媳妇自己找,房子自己买,他们注重的是人品和能力,大大减轻了父母的思想负担。担当和付出迎来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阿黄在绳子的牵制下,皮包骨头,但它的崽子们个个虎背熊腰,被看养户抢了个精光,成了家庭的宠物。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