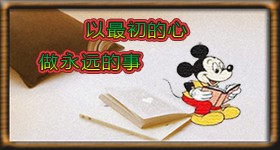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流年】西口五韵(小说)
【流年】西口五韵(小说)
![]() 西口韵又名五字锦,是二人转里带有抒情性的叙事板腔……
西口韵又名五字锦,是二人转里带有抒情性的叙事板腔……
——题记
小村还在。那条河也在。
太阳照例从东边爬出来,在小村上空画一道弧线,沉到村子西边的河里去。那河是霍林河,从内蒙的霍林郭勒漫过科尔沁大草原流到吉林的松嫩大地,不知它淌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转了多少弯弯绕,才在小村这块土地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那小村,就在霍林河即将要汇入松花江的一个拐弯的地方。太阳沉下去的每个傍晚,红霞洒满水面,折射起一片红光,披了小村一身。小村变成橙黄。村后的河水一波一波掀过,河里的芦苇一浪一浪涌着,水草的香气和炊烟的味道一起在小村上空缠绕。马的嘶鸣,狗的狂叫,鸡从树杈飞到墙头,使小村更像小村。
我爷爷在世的时候,总和我讲,说他爷爷兄弟几个搭伴儿挑着挑子从山东那边逃荒过来,一眼看中了这儿,就是因为这的地肥,还有条河。老辈人都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爷爷的爷爷那时候肯定是想,霍林在蒙语里被解释为美食,那霍林河就是美食之河的意思喽,就算这土地长不出粮食来,守着这条河也饿不死了。更何况,那么好的土地,不知被大自然滋养了多少个春去秋回,啃一口泥土都能嚼出油来,怎么会长不出粮食来呢?
我爷爷的爷爷是第一个在这霍林河边上搭起窝卜,生火起灶过日子的,过得久了,他有了儿子,有了孙子,原来没有人烟的荒草地里有了人气。赶脚的路过,会问,姓啥的?
答说,姓胡。
那小村子就叫胡家村了。外人再提起时,都觉得那胡家村确实不错,水美,鱼肥,粮食也产的多,就接二连三有胡姓以外的姓氏投奔过来,村子变得越来越大,大到胡家的姓氏很快就被湮没了,小村变得人来人往,新人换旧人,再提起它,年轻的总要问一问,为啥叫胡家村呢?年老的就要出来费一点口舌才能说得清楚。算算,它有二三百岁了。
二三百岁,多少人和事都憋了满满一肚子,随便扯下一根胡子,都能带出一沓故事来。
不扯远的,就说说我从小见到大的这五个人吧。五个人,足可以凑一台拉场戏了。
但我一个一个数,他们唱的是单出头。
六子
女:我好比高山那个灵芝草啊!
男:哟!把我比作啥呀?
女:你好比臭蒲洼里的癞蛤蟆呀!
胡家村在霍林河边上,我就出生在那。那个小村地势属于陡坡状,村子建得很特别,不在陡坡之上,也不在陡坡之下,正好在陡沿儿上。如果在夜里,远远看,会发现村子上下亮着两层灯火,很美,像城里的二层小楼。不过,最美的,还是环绕村子的霍林河。我很小的时候,河面上翻滚着芦苇荡,成百上千的白天鹅常常在水上驻足,河里有鲶鱼﹑鲫鱼﹑鲤鱼﹑胖头、泥鳅……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鱼特逗,也不知道是因为长相老成还是怎么,村里人都把它们叫作“老头鱼”。因为这条河,村里的男人大多是打鱼的高手。河水养活了村子里大部分人。
那时候,每天清晨,我从矮墙爬上屋顶,看见河边宛如小小闹市,各地的人聚在那里开鱼。车来人往,好不热闹!六子,是最抢眼的一道风景,鱼打得精,每天都倒背着手在河边乱转,嘴里的小调飘得满村都是。
那小小的村子,我从来不觉得它美,数不尽的鱼,让我从来不觉着鱼是一道美食。我父亲总是在炊烟一起,就跑去河边拎回二斤鱼来,让我母亲趁着新鲜炖了,我为此常常和他吵架,觉得一天至少两顿鱼的日子简直是一种折磨。
后来,掺着浓浓乡情的臭鱼烂虾是我再也无法品尝的美味佳肴。河水干涸了,渔网成堆成堆废弃在院子里,大部分以渔为生的人去城里打工了。小村子一下子安静下来,迁走的村民掀去了房顶的檩木,独留黄土堆砌的框架子,在我一天一天长大的过程中,一年一年矮下去。
村子里,唯有六子的心情没有因为河水的干涸而受到影响,二人转依旧唱着,还不停地说人的命,天注定,瞎琢磨个球。
六子家在村子的西北角,两间土房低得一脚踏进去,像是踏进了黑窖里。墙面上有一道道沟痕,雨水冲刷后留下的,似乎多少年来都未曾抹过一把泥。路过他家门口,会有一股酸臭味随风袭来。有的女人爱干净,就会一手捏住鼻子,一手在眼前扇来扇去。六子有个傻大哥要是看见了,一个箭步冲过来,对着路人,用憨里憨气的声音大声嚷嚷,你再敢捂鼻子,我放狗咬你。说完真的就回头叫狗,狗疯了似的把前爪搭在墙上,对着路人狂叫。
村里的女人不叫他傻子,叫他半拉子,他放狗乱叫,女人就会骂,你个死半拉子!弯腰拾起半块砖头扔过去。傻子一下子就哭了,对着屋子里喊,爹,我不是半拉子!
六子爹左腿有点瘸,走起路来却一阵风,披一件旧衣服,油油的,亮亮的,一颠一颠跑出来,对着傻子吼一声,老大,给我回屋去!傻子就噘着嘴,抖抖肩,用袖子在乱糟糟的胡子上抹一下,再踢狗一脚,乖乖钻回去。
六子爹跟进来,会问他,六子呢?他会说,谁知道又跑谁家蹭饭去了?
这是常事。六子一天到晚没啥事儿,早晨从被窝子里爬出来就到大街上溜达,猜准了谁家的活计忙,就凑近院子,与人搭讪。碰见了谁,人家若都不说什么,六子就哼着小调,甩着步子,手插在衣兜里,继续满街晃悠。
总会遇到有人问,六子,今儿没事?六子说,忙着呢。那人要说,家里有点活忙不过来了,求你六子帮个忙呀,中午正好喝两盅。六子就很爽快答应说,也行啦,我先回家吃了早饭就来。那人马上会把他迎到屋子里,怕他回家吃饭的空儿又被别人在路上劫去了。不过,吃饭之前,女人会端来一脸盆子热水,说,六子,洗把脸,精神精神。六子就把一脸盆子水洗黑了。
六子是个巧人,会木匠活,瓦工、修理村子里高级四轮车,还会点电焊,是村子里的香饽饽儿。胡家村要是没了六子,估计比口袋里没钱还难受。难受在哪儿?难受在求六子一壶小酒就搞定的事儿,求别人不行。
六子差不多天天被小酒醉得红扑扑的,从别人家里出来,踱着方步子,一手插在衣兜里,一手捏着一根笤帚棍儿剔着牙,嗓子眼儿里哼着二人转,小曲句句在调上。村里人逗他,六子,唱得好呀!
六子得意起来,那是,想当年差一点就靠唱二人转吃饭了,县剧团团长嫌我长得丑,愣是瞎了咱这副好嗓子。边说边在脸上抓,惹得人一边走一边笑,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喊一句,六子,明儿来家喝酒呀,顺便帮我修一下四轮车。六子赶紧端起架子来,说,明儿我忙着呢。那人说,耽误你一天,哥实在是弄不走那个笨东西。六子就装得很无奈,说,也行吧。
六子喊我父亲大哥,我跟着父亲叫他六子。别人也都叫他六子,包括我以外的所有小孩子。六子有事没事总往我父亲那里跑,有活没活我父亲都留他吃饭。他若在家里吃饭,即便母亲会烧上一水缸的水,把他扔在里面泡上两天,我也定不上桌。父亲拿眼睛瞪我,我一转身,一跺脚,捧着饭碗,躲进厨房里,不愿再出来。六子不在乎,照样把盘子里的菜尝个遍。
那个时候的六子,三十多岁。我常听父亲和他说,六子,给你介绍个媳妇吧,带个孩子,行不?六子说,我才不养别人的种呢。父亲骂他,你能什么能?人家愿不愿意跟你还不一定呢?六子就耷拉着脑袋说,我要是娶媳妇了,我爹他们就没人管了。
六子在我父亲的怂恿下还真去相过一次亲。记得那天父亲给他理了头发,刮了脸,母亲还找出父亲的干净衣服给六子换上。利索的六子并不情愿地出了门,我看着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直心疼我父亲的那套衣服。
果真,没超过五天,六子垂眉丧眼儿回来了,像是病了一场,大伙问他咋了?他说是惦记他那瘸腿的老爹和那个傻哥哥。
从那以后,谁都不再提给六子保媒的事了。六子自个也不惦记。他把自家的几亩地承包出去,靠拿政府的救济款和开一个修理铺过日子。手头宽绰了,钱全都揣在兜里,人多的地方,啐一口吐沫在手指头上,一张一张数。有人说,嗨,六子,满屯子人,你活得最潇洒。六子头也不抬摆弄着手里的钞票,我没老婆没孩儿的,咋自在咋活。这时要是再有人说,六子,有些活计忙不过来咧,求你帮个忙。六子就冒出一句,明儿我忙。人家说,你有啥忙的?帮帮忙嘛,六子。六子就不耐烦了,说,明儿再说,明儿再说。任村里人再说上一箩筐的好话再加上一桌子的好酒好菜,六子也不动心,反过来他会对别人讲,想拿我当免费的使吗?我六子除了缺女人,啥也不缺。
六子爹九十岁那年死了,对六子的打击相当大。六子说,爹,你可不能死啊,国家政策规定,过了九十还给钱呢,咱可要好好活着啊。六子一包一包往回买药,旁人说,六子,孝顺。六子说,自个儿的爹,得好好疼。争取让他活到一百岁。
可六子爹吃了很多药也不顶用,六子就把他爹抬到乡卫生院,六子对大夫说,可要救活我爹呀,这可是我们家的财神爷。大夫眨巴眨巴眼睛说没救了。六子就哭得撕心裂肺的。
政府给贫困户盖房子,六子家的大瓦房,三间,蓝盖,瓦蓝瓦蓝的。有个叫刘三的逗六子,有房了,弄个媳妇吧。六子说,我才不稀罕。可是,那年夏天,刘三去河对岸的一个庄户人家打工,回来对六子说,六子,我给打工的这个东家是个女的,男人死了,那女人和你年龄差不多,五十来岁,长得不老相,还大高个儿呢。
六子眨巴几下眼睛岔开话问,明儿你们去多少人给她铲地?刘三说,越多越好!六子滴溜溜转了一圈眼珠子说,铲地也不累,明儿我也随车去,挣几张票子。刘三哈哈大笑说,你六子也缺钱?六子才不管那些,第二天早早在四轮车斗里占了个好位置。
说是铲地,实际上是女东家把黄豆种在了河床上,河水早就没了,河床肥沃,黄豆地里长满了杂草、水蒿子,还有芦苇,要用镰刀去割下来,根本不能用锄头去铲,这样反倒更轻松。找一个干活稳当、麻利又不毛糙的男人领队,其他人跟在打头阵的后面,好好干,不打狼,东家就会很满意。
六子去了,干着活,时不时瞄女东家几眼,大高个儿,头发烫着卷,一脸富态相,连个褶子都没有。六子心里喜欢得不得了,越干越来劲,把领队的都落在了后面。
女东家在后面偷偷问,那人是谁?刘三在心里骂着六子,嘴上却说,六子可是我们村的童男子,力气大着呢,有使不完的劲。是不六子?
六子头也不抬,弓着腰很卖力地割苇子。刘三又喊,六子,来一段二人转吧,女东家最爱听。所有的人就都跟着喊,六子,来一段,听你的二人转干活不累。六子回过身来,清清嗓子,眼睛溜着女东家说,来一段?哈哈,那我就来一段《蓝桥》吧。说着站在黄豆地中央,就唱上了:
红缎子来吊面啊,
大绒啊来镶边哪,
上有几出戏呀,
有戏咱们俩就慢慢演啊……
六子一边唱,一边摆姿势,女东家听得豪爽,看得大笑,最后还伸出大拇指说,六子唱得好!六子就唱了一个又一个。
女东家说,六子唱得好,活也地道,下午六子领队。六子美得午饭都没吃好,下午早早把人都领到地里干活去了。刘三骂六子缺心眼,第二天再去上工,说啥也不让他上车,六子就天天骑着自行车去。
刘三知道六子的心思,见到女东家就喊,东家,六子可是有钱的主,是我们村的钻石王老六,电焊工啊,修理铺子开得老大了。女东家看了看六子问,六子,你的铺子投资多少钱?六子很得意,说,我要全弄完怎么也得个五六万。刘三正举着水壶仰着脖子往肚子里灌水,听六子这么一说,一口水喷得满天都是。
女东家的活几天就干完了,六子的心却长了草,天天骑着自行车往河对岸跑。村里人问,六子,天天往对岸跑干啥?六子说,我去河里打鱼呢。村里人说,河都干了,哪来的鱼?是去打野鸡了吧?六子不回答,岔开话说,我看到芦苇荡里还真跑着野鸡呢。村里人就哈哈大笑。
暑伏,村里人最闲,男人女人成帮结队蹲在墙角下,女人在阴凉里纳鞋底,男人打扑克。六子也来凑热闹,手里多了个手机。那年头手机刚兴,墙根儿下的人齐刷刷看着六子,没几分钟那东西就要唱一下,六子就把它放在耳边,一会儿说一会儿笑,一会儿又骂上几句。快嘴的女人抢先问,六子,真能哎,哪来的手机?
六子笑而不答,很神秘。女人们互相递个眼神,一拥而上,把手机夺下来。六子说,别弄坏了呀,这可不是一般人送的。女人们追着问,谁送的?不是对岸的那个女人送的吧?
六子又装得神秘兮兮的。女人们更加好奇,你俩好上了?真的好上了?
六子说,早好上了,我一去,她就把我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不信?看看这衣服!说着随手在衣襟上掸几下。村里人看了看,六子确实变化了,比以前干净了。
六子的手机又响了,拿着它的女人吓了一跳。六子一把夺回来,往人群外站站,放在耳边嘻嘻哈哈地说。
有人说,六子,谁打的电话?不会是对岸那个女人吧?六子又笑,却不回答。
六子的电话唱得太频,接电话时说几句就急了眼,很威风。
六子地位的卑微角色的关键;香兰姐妹命运的坎坷让人心疼;秀珍对丈夫的一往情深令人唏嘘……五个章节,五种情怀。故事之间虽然情节各个不尽相同,但内在的主线却都是讲述着从底层小人物真实的悲欢离合,几个故事共同构成了一个乡村的陈年过往,人性的温暖阴暗。